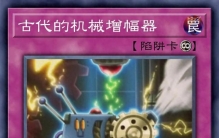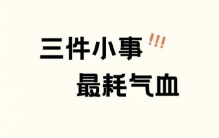创造的本质是什么?
开创意义治疗学派的心理学家维克托·弗兰克认为,“创造”是发现生命意义的途径。创造即是通过某种类型的活动实现个人价值。创造彰显出我们的生命力,在童年时期几乎每个孩子都具有创造力,我们会编故事、发明游戏、随心所欲地画画。但随着不断被各种条条框框规训,我们的创造力可能被磨灭。那么创造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创造的本质是什么?
奥利弗・萨克斯在他的随笔集《意识的河流》中梳理了这些问题。他曾经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内科学教授,被誉为“医学界的桂冠诗人”。作为一位神经科学家,他一直探寻人类行为的神秘莫测之处。这本随笔集涉及认知、学习、记忆、情感、注意力、意识、睡眠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本文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意识的河流》,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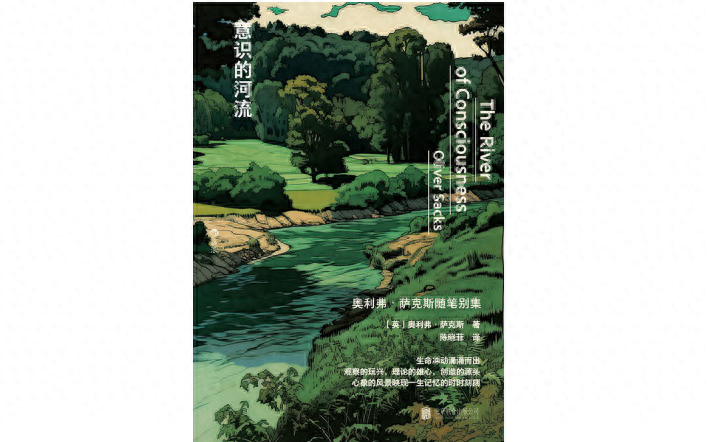
《意识的河流》, [英] 奥利弗·萨克斯 著,陈晓菲 译,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7月。
模仿是创造的起点
所有孩子都沉迷于游戏,这既是重复和模仿,也是探索和创造。他们同时被熟悉之物和不同寻常之物吸引——一边牢牢锚定在已知和确认之物上,一边渴求新鲜和从未经历过的东西。儿童对知识和领悟、对精神食粮和刺激怀有一种原生的饥渴。他们不需要被说动或者“被鼓动”才会去玩、去探索,因为和所有富有创意或原创性的活动一样,玩本身就能让人发自内心地愉悦。
创新冲动与模仿冲动在假装游戏中合二为一,这种游戏的玩法通常是用玩具、玩偶或者真实世界的微缩模型来演绎新的场景,也可以彩排或重演旧的场景。儿童被叙事吸引,不仅向别人索求故事、品味故事,也自己编造故事。讲故事和制造神话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手段。
缺乏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智性、想象力、天赋、创意将无用武之地,也正因为如此,教育必须充分结构化,有的放矢。但是教育如果太过僵硬和形式化、缺乏叙事性,就会抹杀儿童一度活跃和充满好奇心的大脑。教育必须在结构和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不同儿童的需求可能有着天壤之别。有些年轻的心灵可以在良好的教育下茁壮成长。
有些儿童(包括最有创造力的那些)可能会抵制程式化的教育,他们本质上是自学者,永无餍足地渴求以自己的方式学习和探索。大多数儿童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历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需要结构化,同时也需要或多或少的自由。
尽管贪婪地吸收同化和模仿各种模型本身不是创造,但往往预告了未来的创造力。艺术、音乐、电影和文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特殊的教育,丝毫不逊于知识和信息,这就是阿诺德·温斯坦所说的“感同身受地沉浸在他人的生命中,由此获得新的眼睛和耳朵”。

纪录片《关于苏珊·桑塔格》(2014)剧照。
对我这代人来说,这种沉浸主要通过阅读实现。苏珊·桑塔格在200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谈到阅读如何在她年幼时为她打开了整个世界,延展了想象力和记忆的地平线,远远超越自己实际的、直接的个人经验。她这样回忆道:
我五六岁就阅读了艾芙·居里(Eve Curie)给她母亲写的传记。漫画、字典、百科全书,我一视同仁,全都读得津津有味……就好像我吸收的东西越多,我就变得越强,看出来的世界就越博大辽阔……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天分极高的学生,一个天分极高的学习者,一个顶尖的自学儿童……这是创造吗?不,这不是创造……(但是)并不妨碍它之后变成创造……我狼吞虎咽,而不是勤于产出。我是一个精神上的漫游者,精神上的贪食者。我的童年,除了悲惨的现实生活之外,唯以狂喜为业。
这段话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蕴含的能量,那饥渴难耐,那热情如火,还有爱。凭着这些,年轻的心灵向往所有能够滋养它的东西,寻求知性或其他方面的楷模,通过模仿来磨砺自己的技能。
她广纳博览的知识来自其他时空,关乎人类本性和经验的多样性,这些观照事物的角度在激发她本人的写作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我大约7岁时开始写作。8岁时我办了一份报纸,填入故事、诗歌、戏剧和文章,以每份5分钱的价格卖给左邻右舍。我担保它很平庸,因循守旧,单纯地编编东西,受各种东西影响,其中就有我当时正在阅读的书……我当然有楷模,有一整座万神殿……如果我在读爱伦·坡的小说,我就会写出爱伦·坡风格的小说……我10岁的时候,卡雷尔·恰佩克(KarelČapek)一部被遗忘很久的关于机器人的剧本 R.U.R(“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的缩写)正巧落到我手上,于是我写了一部关于机器人的戏。但这完全是衍生品。我读什么就爱什么,只要爱上就会想要模仿——这未必是通向真正的创新或创造性的正道;但就我所知,也不会妨碍它到达那里……我13岁时就开始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
桑塔格的早慧和天纵奇才使她连跳几级,小小年纪就跻身“真正的”写作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模仿、见习期和学徒阶段才能达到这个段位。这是一段挣扎着发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声音的时期,是一段实践和重复、精纯技艺并使之臻于完美的时期。

纪录片《关于苏珊·桑塔格》(2014)剧照。
有些人经过这样的见习期,可能会一直停留在精纯技艺的阶段,再未能进阶到重大创新的层次。即便从时间上拉开一段距离回看,我们也很难判断,从有天分同时又是衍生物的作品跃升到重要创新,这个转变究竟发生在何时?该在哪里划下界限,来分隔影响和模仿?是什么把创造性的吸收、挪用和亲身体验的深度纠缠,与单纯的模拟区别开来?
模拟、模仿和拟仿
“模拟”一词可能暗含某种意识或意图,但模仿、回映(echoing)、镜像是能在所有人类以及许多其他动物(所以才会有诸如“鹦鹉学舌”“沐猴而冠”这样的词语)身上看到的普遍心理(事实上也是生理)倾向。对一个婴儿吐舌头,他就会镜像这个行为,即便此时他还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肢体或者形成较为完整的身体意象—终此一生,这种镜像反应始终是我们重要的学习模式。
梅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在《现代心灵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Mind)中将“模拟文化”视为文化演化与认知演化中的一个关键阶段。他在模拟(mimicry)、模仿(imitation)和拟仿(mimesis)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
模拟的特点是一板一眼,尽可能分毫不差地还原。因此,完全复刻某个面部表情,或像鹦鹉那样完全复制另一只鸟的叫声,这些都是模拟……模仿没有模拟那样刻板;子代复制亲代的行为,模仿而非模拟父母的行为方式……拟仿在模仿的基础上增加了表征的维度。它通常将模拟和模仿结合到一个更高的目的上,也就是将事件或关系重演出来。
唐纳德认为,模拟存在于许多动物之中;猴子和类人猿更多是模仿;拟仿则是人类独有的。但是,这三种状态可以在我们身上共存或重叠——一种表现,一个行为,都可能同时具备这三种要素。
在某些神经条件下,模拟和复制的力量或许会被放大,或者更少受到抑制。患有图雷特综合征、自闭症或某种大脑前额叶损伤的病人,可能会无法抑制地镜像或回映他人的言语与行为;有时候回映的可能是声音,甚至是环境中毫无意义的声音。在《错把妻子当帽子》里,我描述了一位患图雷特综合征的女性,她走在大街上会回映或模仿车头那个牙套似的水箱罩和状似绞架的路灯,还有过路行人的姿势和步态—通常带有某种漫画式的夸张。

《错把妻子当帽子》,[英] 奥利弗·萨克斯 著,黄文涛 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5月。
有些自闭症患者(或称学者症候群患者,有认知障碍但在某方面拥有超常能力的人。)拥有异乎常人的视像化和复述能力。我在《火星上的人类学家》里详细描述过的斯蒂芬·威尔特希尔(Stephen Wiltshire)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斯蒂芬是个视觉学者,在捕捉视觉相似性上有惊人的天赋。无论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参照、无论当场发生还是事隔很久,在他这里区别都不大,感知和记忆似乎不可分割。他还有一对天赋异禀的耳朵;小时候,他会回映噪音和话语,好像没有任何意图,也没有自我意识。青年时代,他去了一趟日本,回来后开始发出“日式”噪音,胡诌着假日语,做出各种“日式”手势。他可以模仿任何他听过的乐器,拥有高度精确的音乐记忆。
斯蒂芬16岁时,有一次我很惊讶地听到他假唱汤姆·琼斯(英国歌手)的《不足为奇》(“It’s Not Unusual”):只见他摇晃屁股,舞动着,比画着,把想象出来的麦克风握在手里递到嘴边。在这个年纪,斯蒂芬通常不太显露情绪,经典自闭症的外在表现他都有:歪脖子、抽动、茫然无焦点的视线。但是,这些在他唱起汤姆·琼斯的歌时统统消失了——消失得如此彻底,让我不禁怀疑:他是否已经以某种神秘离奇的方式超越了模拟,真正与这首歌的情绪和情感产生了共鸣?
这让我想起在加拿大遇到的一个自闭症男孩,他在心里记下一整部电视剧,每天都要“重播”好几次,配上所有的对白和动作,甚至连掌声也不落下。我曾把这看作一种自动的浅层复刻,但是斯蒂芬的表演令我困惑沉思。难道他已经从模拟进入了创造或者说艺术层面?他是有意识地或者有意图地共享了这首歌的情绪和情感,还是单纯地复制—又或是介于两者之间?
(在有学者症候群的自闭症患者或心智障碍者中,记忆力和复述能力可能很强大,但是所有内容会被当作某种外部的东西留存在记忆中,和他们自身的理解无关。1862年,约翰·兰登·唐——唐氏综合征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写过一个有学者症候群的男孩,称他“读书过目不忘”。有一次,唐给了他一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男孩流利地阅读和背诵,但不涉及任何理解,在第3页时,他跳了一行,然后又回过来纠正了自己。“自那以后,”唐写道,“每次当他通过记忆来背诵吉本的庄严词句时,他都会跳过那一行,然后回过头去纠正错误,规律得好像书上原本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写的。”)
另一个自闭症患者(也出现在《错把妻子当帽子》里)经常被医院员工描述为复印机。这不公平,有点儿侮辱人,而且不准确,因为学者症候群患者记忆中所保留的细节完全不能与机器式的记忆相提并论;这里涉及对视觉特征、言语特征、姿态特异性等的区别和辨认。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东西内含的“意义”没有被完全吸纳,所以和我们的记忆相比,学者症候群患者的记忆看起来更为机械。
所有艺术都是作为“衍生物”开始的
如果说模仿对艺术表演很重要,那是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坚持不懈地练习、重复和彩排至关重要,对绘画、作曲或写作领域来说同样如此。所有年轻的艺术家在学徒阶段都曾寻慕楷模,从他们的风格、匠艺和创意中得益精进。年轻的画家可能流连于大都会博物馆和卢浮宫的画廊,年轻的作曲家可能会去听演奏会或精研乐谱。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艺术都是作为“衍生物”开始的,就算不是直接模仿和改写,也深受其慕仿对象的濡染和影响。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3岁那年曾求问于威廉·沃尔什(William Walsh),他很敬仰这位比自己年长的诗人。沃尔什对蒲柏提出的建议是“准确”。对此,蒲柏的理解是,他首先应当掌握诗歌的形式和技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列了一个“英国诗人模仿”计划,最先选择的就是沃尔什,继而是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罗切斯特伯爵,还有乔叟、斯宾塞这样更重量级的诗人;还有一种类型的作品,他称之为对其他拉丁语诗人的“意译”(Paraphrases)。
17岁时,蒲柏已经掌握了英雄双行体,着手创作他的“田园诗”及其他作品,在其中发展和锤炼自己的风格,但止步于最乏味或最陈词滥调的主题。只有在能够自如地运用诗歌的风格和形式之后,他才开始加入那些精妙绝伦、有时候甚至令人惊叹的想象力的产物。或许对大多数艺术家来说,这些阶段或过程重叠的部分颇多,但是只有先模仿形式或技术,并打磨精通,才有可能做出重大创新。
然而,即便是经年累月的准备和磨砺,天纵之才是否能够实现他的天赋依然是未定的。无论是艺术家、科学家,还是厨师、教师或工程师,许多创意工作者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余生安于一技或者严守边界,绝不会破旧迎新。即使没有再进一步到达“重大”创新的境界,他们的作品依然会展现出技术上的圆熟甚至精纯,令人欣悦。

电影《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2005)海报。
有很多关于“微小”创新的例子,指的是那种最初被表达出来之后,其特征不会有显著改变的创造。亚瑟·柯南·道尔写于1887年的《血字的研究》是一桩了不起的成就,也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系列的第一本,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侦探故事”。五年之后,《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集》获得空前的成功,柯南·道尔发现自己打造了一部具有无限延展性的系列作品。这让他既高兴,又有点羞恼,因为他还想写历史小说,但公众对此兴趣缺缺。他们想要福尔摩斯,想要更多的福尔摩斯,作者必须提供。柯南·道尔甚至已经在《最后一案》中杀死福尔摩斯,把他送去莱辛巴赫大瀑布与莫里亚蒂决一死战,但公众坚持让福尔摩斯复活,于是柯南·道尔也真的在1905年的《福尔摩斯归来记》里让他复活回归了。
就手段、心智和个性而论,福尔摩斯没有太大的进步;他没有老去的迹象。没有案子的时候,福尔摩斯这个人几乎不存在—或者不如说,以一种退避的方式存在:拨拉他的小提琴,吞吐可卡因,倒腾他那些恶臭难当的实验—直到下一个案子召唤他出场。
那些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可能是19世纪90年代写的,而那些写于19世纪90年代的故事即便放到以后也不会过时。福尔摩斯的伦敦和他本人一样一成不变,皆脱胎于19世纪90年代。柯南·道尔自己也在1928年出版的《福尔摩斯短篇探案集》的序言里写道:读者可“以任意顺序”阅读这些故事。
创造需要无意识的准备
每100个在朱丽叶音乐学院学习或者在各大实验室受业于名师的青年才俊中,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可以谱写出令人难忘的乐曲或者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是否其中大多数人尽管拥有天分,却缺乏进阶的创造灵感?他们欠缺的是否不是创造力,而是那些对获得创造性成果来说不可或缺的特质—比如大胆、自信、独立思考?
习惯于固守成规之后,若想开辟新的道路,光有创造潜能是不够的,还要求具备一种特殊的精气神,一种特殊的蛮勇或叛逆。这是赌博,和所有创造性计划一样,因为这个新方向上很可能不会结出任何果实。
创造不仅要求经年累月有意识的训练和准备,还有无意识的准备。这段酝酿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为了把个人受到的影响和资源吸收并同化到潜意识里,经过重新组织之后,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在瓦格纳《黎恩济》(Rienzi)的前奏曲里,你几乎可以完整地追溯这个过程。那里有对罗西尼、梅耶贝尔、舒曼以及其他人的回映、模仿、意译和拼贴。然后,猝不及防地,你听见了瓦格纳自己的声音:如此有力,如此与众不同(尽管在我看来是可怕的),一个天才的声音,前无古人、横空出世。照搬挪用与吸收同化,关键区别在于深度,在于意义,在于积极的个体化的投入。
1982年初,我意外收到一个从伦敦发来的包裹,里面有一封哈罗德·品特(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信,还有新剧《一种阿拉斯加》(A Kind of Alaska)的手稿,据他说灵感得自我在《苏醒》里写到的某个病例。品特在信中说他1973年就读了该书的初版,立刻开始琢磨把它改编成戏剧可能遇到哪些问题,但因为当时没有想到好的解决方案,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八年后的某天早上,他带着这部剧的第一幅画面、第一个句子(“有些事在悄然进行”)的清晰烙印醒来。接下去的日子里,这部剧开始“自动书写”。我情不自禁地拿它和一部我四年前收到的剧本(灵感得自同一个病例)做比较,那位作者在一同寄来的信里说,他两个月前读了《苏醒》,表示“深受影响”“极为着迷”,令他不由自主地想要马上动手写剧本。我很喜欢品特那部戏,尤其是它引发了这样深刻的变形,将我的主题“品特化”了。但1978年的那个剧本我感觉总体上是衍生性的,因为它有时候会从我的书里整句整句地照搬,连应付一下的改动都没有。在我看来,它不像一部原创戏剧,更像是抄袭、山寨或者戏仿(虽然作者的“着迷”或者说好意是毋庸置疑的)。
我不确定该怎么理解这件事。是因为偷懒、缺乏天分或原创性,所以才没有对我的作品进行必要的改动?抑或是,这本质上是个酝酿期的问题,他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让阅读《苏醒》的体验沉淀下来?他也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忘记它,让它沉入无意识,在那里与其他经验和思想连接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周围文化的产物。观念散布在空气中,我们经常会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挪用时代特有的表达和语言。我们借用语言,而不是发明语言。我们发现它,慢慢长成它的样子,尽管我们可能以高度个人化的方式使用它、诠释它。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事实上的“借用”或者“模仿”,而在于如何利用借用、模仿和汲取的东西,在于吸收到多深的程度,与自己的经验、感受和思想融合,与自我关联,用全新的、属于自己的方式加以表达。
在获得深刻的科学或数理洞察之前,时间、“遗忘”和酝酿是同等重要的先决条件。伟大的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在他的自传里回忆如何与一个特别困难的数学问题角力,却因徒劳无功而深感绝望。1他决定休息一下,来一趟地质之旅,将注意力从数学问题上引开。然而有一天,他写道:
我们上了一辆马车,准备去某个地方。就在我踩上踏板的瞬间,突然灵光一闪,在此之前没有任何铺垫:我以前用来定义富克斯函数的变换,等价于那些非欧几何的变换。我没有验证我的想法;我应该没那个时间,因为……我接着一段已经开始的谈话继续聊着,但是心中无比确定。回卡昂的路上,为求心安,我抽空核实了结果。
过了一阵,他去了海边,又“假装”在另一个问题上碰了钉子,他在那里写道:
一天早上,在悬崖边散步时,一个想法浮上心头,同样具有简洁、突然以及即刻确定的性质:不定三元二次型的算术转换和非欧几何的算术转换完全一致。
很明显,就像庞加莱所写的那样,一定存在积极的、密集的无意识(或者说潜意识、前意识)活动,哪怕在问题完全被抛诸脑后,头脑一片空白,抑或是被其他事情分心的时候。这不是动力论的无意识,或者“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抑制不住地翻腾着被压抑的恐惧和欲望;也不是“认知论”上的无意识,让我们在没有意识到自己如何做到的情况下开车,或者说出符合语法的句子。庞加莱的无意识,是完全隐蔽的创造性自我在酝酿如何完成高难度的任务。庞加莱向这个无意识的自我致敬:“它并非纯粹自动;它明察秋毫……它懂得择选,神机妙算……它比有意识的自我更灵通,因为它在失败之处成功。”
一个问题酝酿许久,答案突然袭上心头,这种情况有时候可能出现在梦中,或者半清醒的状态下,比如临睡前一刻或醒来不久,此时的思维怪异地自由发散,有时还伴有这种状态下常见的近乎谵妄的意象。庞加莱写道,一天晚上,就在这种浑浑蒙蒙中,他似乎看到一个个念头在眼前移动,像一种气体的分子,偶尔相互碰撞、两两结对,扣连在一起形成更复杂的观点—眼前这幅罕见的景象(尽管有人描述过类似的景象,尤其是在药物引发的状态下)就是通常不可见的创造性无意识过程。

德国作曲家理夏德·瓦格纳。
瓦格纳也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莱茵的黄金》(Das Rheingold)的序曲是如何由来的。当时他也处在一种古怪的、半谵妄的昏蒙状态之下,经过漫长的等待,灵感翩然降临:
熬过激情无眠的一夜,第二天我强迫自己在重峦叠嶂、满布松树的乡间久久地散步……下午回来后,我在坚硬的沙发上摊开手脚,累得半死……就在这昏沉蒙眬中,我突然感觉自己沉入了湍急的水流。冲刷的水声在我的大脑里变成了音乐,降E大调和弦,持续不断地搅碎打散,重重回响;这些破碎的形式似乎是节奏断变快的旋律乐段,虽然那个纯粹的降E大调三和弦始终不变,但它的连绵不绝仿佛在我沉入其中的元素上附加了无穷的意义……我立刻辨认出“莱茵的黄金”的管弦乐前奏曲,长久以来一直潜藏在我心里……此刻终于向我展露真貌。
(像这样在梦中突然得到科学发现的故事有很多,有些很典型,有些可能被神化了。伟大的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据说是在梦中发现了元素周期表,醒来后立刻草草记在一个信封上。信封是真实存在的,目前看来,这个故事或许是真的。但是这让人误以为天才的灵光仿佛信手拈来,而事实上,自1860年在卡尔斯鲁厄参加学术交流会之后,门捷列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这个课题里浸淫了至少九年。他显然完全被这个难题迷住了,在横贯俄国大地的火车上,他把大把的时间花在一套特制的卡片上,在上面写下每一个元素和它的原子量,玩着把元素打乱、整理再重组的“化学纸牌”游戏。然而,最终的成果是在他没有刻意寻求的时候降临的。)
我们是否能够利用某种尚未发明出来的脑功能成像技术,来区分自闭症学者的模仿或拟仿与瓦格纳那样的深层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转换?逐字记忆(verbatim memory)在神经学意义上是否不同于深度的、普鲁斯特式的记忆?我们是否可以证明,某些记忆对大脑发展和脑回路的影响微乎其微,某些创伤性记忆却固着下来、持续活跃,另一些记忆则变得整合贯通,在大脑中引发了深刻的、创造性的发展?
在我看来,创造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想法在其中化为湍流,致密迅捷,伴随着无与伦比的清晰度和意义涌现的感觉。创造在生理上也有显著的特征。我认为,如果我们有能力开发出更高清的脑成像技术,可以从上面看到由无数连接和同步构成的不同寻常且分布广泛的活动。
在这样的时刻,在我写作的当下,思想仿佛自动连贯起来,即时披上恰当的言语外衣。我仿佛可以绕开或越过自己的大部分人格特质,我的神经症。它可以不是我,同时又是我内在最核心的部分,无疑也是最好的部分。
原文作者/[英]奥利弗・萨克斯
摘编/荷花
编辑/王菡
导语校对/王心
大家都在看
-
游戏王卡牌分享 古代的机械系列2 明明可以打正面却偏要耗血玩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依旧是古代的机械系列,不过跟之前的分享的以古代的机械巨人为核心不同。古代的机械系列大多都有攻击时魔法陷阱封锁的效果,所以刚正面是一点也不怂。但是小编看了一下许多配合的魔法陷阱,竟然有很 ... 机械之最04-27
-
古希腊的“天书”:安提基特拉机械消失之谜 1901年,希腊海绵潜水员在安提基特拉岛附近的一艘古罗马沉船中,意外发现了一块不起眼的、严重锈蚀的青铜块。起初,它被忽视了,混在一堆雕像和其他文物中。但随着时间推移,当锈蚀层逐渐剥落,显露出内部精密的齿轮 ... 机械之最04-27
-
祖冲之:古代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科学家,我们永远铭记 祖冲之,字文远,号冲之,生于公元429年,卒于公元500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工程师。他以其卓越的数学才能和深厚的科学知识,在古代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祖冲之不 ... 机械之最04-27
-
专门Mac设计带数字键盘,手感接近全金属:贱驴K4Max机械键盘分享 前言:对于办公室一族,想要机械键盘的利落手感,又想有传统键盘的高效输入,带数字小键盘的机械键盘无疑是更好的选择。近期,以铝坨坨而被机械键盘爱好者喜欢的贱驴品牌,再次丰富产品体系,推出了专为苹果Mac电脑 ... 机械之最04-24
-
一步到位,最具性价比的国产豪华SUV,试驾问界M8 问界M9的市场表现不必多说,可以称神的存在,进一步下探售价且被给予厚望的”小问界M9”的问界M8是否具有M9那样统治市场的表现?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美丽的丽江试驾问界M8。首先这辆车虽然尺寸上比一众9系产品略小 ... 机械之最04-22
-
“我最在意的身份是教师”——追忆恩师钟秉林 【大家】作者:姜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学人小传钟秉林(1951-2024),北京人。1969年至1973年,在陕西延安插队。1973年至1977年,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求学期间加入 ... 机械之最04-21
-
希捷:机械硬盘环保碾压SSD IT之家 4 月 18 日消息,Blocks and Files 研究机构 4 月 16 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希捷调查了基于碳排放输出的三种最受欢迎的数据存储解决方案。在固态硬盘、机械硬盘和 LTO 磁带三种存储中,机械硬盘被发现是最环 ... 机械之最04-20
-
330余家企业齐聚 “起重机械之都”河南长垣觅商机 中新网新乡4月16日电 (刘鹏 李海珠)以“数智赋能,绿动未来,质赢天下”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国·长垣国际起重装备博览交易会16日在“起重机械之都”河南省长垣市开幕,来自国内外的330余家企业赴此集中展示行业新技术、 ... 机械之最04-17
-
鼓吹"机械至上"的人,真的开过现代车吗? 2024年某地车展上,一位老司机摸着新车的全液晶仪表直摇头:"现在车子整这么多屏幕有啥用?要我说还是机械仪表盘最踏实"。这话听着耳熟吗?从启动钥匙变成手机APP到机械手刹消失,总有人怀念化油器时代的"纯粹机械" ... 机械之最04-15
-
三件小事最耗气血,别再做了! 《黄帝内经》中说:“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意思是说,气血是生命的根本,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运转的机器,气血就是最根本的动力。日常生活中,哪些事情最耗气血,调补气血有哪些好方法?一起来看!(转自:首都中 ... 机械之最04-09
相关文章
- 三件小事最耗气血,别再做了!
- 古董钟表里的机械之美,时光流转中的经典工艺。
- "立木为信"的商鞅,为何成了帝国最锋利的刀?
- 机械革命最划算游戏本来了?配置低但价格给力,国补后3999元
- 宇树机器狗最具有成长潜力的10家企业!一、长盛轴承二、绿的谐波
- 机械之舞:当国产机器人跳出《功夫》的江湖气韵
- 至今无法被超越的经典运输机安225,机械之美超级运输机!
- 一文图解 72 个机器学习基础知识点
- 在皇帝之最中,乾隆独揽了哪三项?
- 机械工程世界一流学科排名:16所进全球前30,上大北理南航闪耀!
- 40岁C罗凭什么被萨哈称为“最完美机器”?退役后必成GOAT!!
- 探寻机械设备领域的“利润巨头”
- 八下物理简单机械之杠杆知识点总结一
- 机械美学:从哈雷到凯旋,百年发动机进化史(基本知识)
- 大罗谈生涯最凶残被铲:对方鞋钉长到像穿高跟鞋,走路像机械战警
- 燕山大学的王牌专业——机械工程,中等生的不二之选
- 尼康相机创造过哪些“世界之最”?——众通社影像
- 各类轴体,75~98键,哪种机械键盘更适合你?自用百元键盘推荐
- 哪个品牌机械手表最耐用
- 机械之美,齿轮运转,动力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