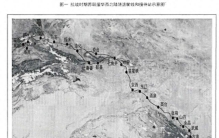文化纵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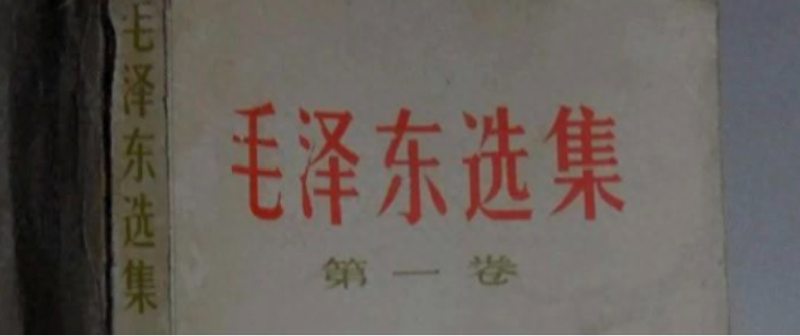 【导读】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国庆日。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革命艰苦斗争的结果,而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也深刻影响新中国的发展。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表述,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本文提出一个关于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新思路,即“三建合一”,建党、建军、建政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作者吴重庆教授指出,将中国革命特性以“农村包围城市”笼统化,仍未触及实质。因为世界其他革命党也有类似经历,但他们往往是一次性起义或长期游击,并没有稳定根据地,也没有自觉的根据地建设。
【导读】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国庆日。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革命艰苦斗争的结果,而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也深刻影响新中国的发展。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表述,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本文提出一个关于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新思路,即“三建合一”,建党、建军、建政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作者吴重庆教授指出,将中国革命特性以“农村包围城市”笼统化,仍未触及实质。因为世界其他革命党也有类似经历,但他们往往是一次性起义或长期游击,并没有稳定根据地,也没有自觉的根据地建设。
作者回顾指出,孙中山强调党政军关系和以党建国,但回避了实质性的土地问题和阶级问题。以孙中山的革命探索为参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超前者。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一改中共中央“尽可能扩大游击区、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策略,认为争取群众与建立政权的过程应同时进行,并不看重地盘一时得失,而是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等)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针对在红军中产生的流寇主义思想,毛泽东认为不应避重就轻地只用流动游击的方法扩大影响,而不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不应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简单路线,而不从地方发展红军;不应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斗争,而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毛泽东强调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但并非固守“土围子”;他反对冒进,但绝非按兵不动,而是主张“波浪式”推进。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认为,如果套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或诸如“政党政治”“军队国家化”等概念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以及今日之党政军关系,不仅全然脱离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人民政权“三建合一”的历史过程和历史事实,而且无视在“三建合一”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人民政权与西方政党、军队及政权之区别。而目前一些研究,对革命史仍停留在社会史研究层面,关注革命的过激行为如何中断了传统或者偏离了社会常态,却连《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里的重要篇章都不愿深入研读并细加引用。这种现象,值得注意。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5期,原标题为《“三建合一”的中国革命道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三建合一”的中国革命道路
近十年来,我一直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给研究生开设“中国革命与毛泽东农村调查”选修课,带领学生精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前半部分(土地革命时期)和《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并结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对历史细节的描述,推动学生重返中央苏区的历史情境,以增进他们对根据地建设的感知与认识。这门课吸引了本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等专业的研究生选修或旁听。重温革命经典,仍然足以激发青年学生的理性与热情。
教学相长,我自己也在备课、讲授以及与学生的互动中,不断加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三建合一”算是我近年来对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一个新概括。“三建合一”指建党、建军、建政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这是中国革命的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表述,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农村包围城市”,这当然是对的。但笼统地说“农村包围城市”,似嫌尚未触及实质。世界上其他革命党也有武装革命的经历,但他们往往是一次性起义或长期游击,并没有稳定的根据地,也没有自觉的根据地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有根据地的革命,根据地是我们党、政、军成长壮大及其特质形成的关键起点,是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之处。
那么,根据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根据地?如何开展根据地建设?
▍孙中山的探索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孙中山先生的探索。孙中山也讨论过党、政、军关系的问题,甚至也有过“根据地”的说法。他追问辛亥革命12年以后,为什么国民政府没有形成,还是军阀在割据?他认为,“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 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党务没有进入军队,党和军没有结合。但他把“党务”较为简单地归结为“宣传”:“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革命以后,大家有了军队,有了政权,以为事在实行,不必注意宣传。岂知革命成功,就只有宣传一道”,“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折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1]他认为,宣传既是党务的内容,也是国民党的革命性之体现。孙中山在将革命党的党务简化为宣传的同时,也极大高估了宣传的作用。“我们国民党就是革命党。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要消灭那一般军阀,军事的奋斗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2]
孙中山认为,党的基础在于军队,所以应当在军队那里做足宣传的功夫,让军队完成心理革命,成为革命的军队,进而完成政治上的革命。“国民党将于一般士兵及下级军官中极力宣传运动,使知真利所在,立成革命的军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3]他还反思,“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所以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之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4]。总之,他冀望靠宣传把党、军、民在意愿、心理、精神上拧成一股绳,从而焕发出革命性和战斗力。
孙中山为此强调以俄为师,“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5]。“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6]“在英美的政治社会,至今还有贫富的阶级。在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象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7]遗憾的是,孙中山把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看得过于简单了:“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全是由于他们革命党都信道笃,拿主义来感化全国,所以没有打什么仗,便把政府根本改造。”[8]“俄之成功,亦不全靠军力,实靠宣传。”[9]当然,他对俄国革命成功作如是观,乃受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诚如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所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10]
孙中山先生探索党政军关系,强调党务,强调党与军队的结合,强调政党的改造(革命党),强调军队的改造(革命军),强调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可是,孙中山先生将此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诉诸宣传,诉诸心理建设,回避实质性的土地问题和阶级问题,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真正有力的、有效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有赖于阶级问题和土地问题的解决。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建设中的“三建合一”
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探索为参照,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确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超前者。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领导的革命同样高度重视党、军、政关系,并且敢于聚焦于土地革命,所以能够把建党、建军、建政融合于根据地建设之中,达成“三建合一”。
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过程,也是争论不断、历经波折的。朱毛红军上到井冈山后,如何开展革命,是打游击并择机拿下沿途城市还是致力于建设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跟当时的中共中央存在严重分歧。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说:“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11]换言之,中共中央希望尽可能扩大游击区,这样才有浩大声势,才有政治影响,而不要去做安于一隅的根据地建设。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说:“他们(指中共中央)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似乎如此一来,革命就大功告成了。但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12]
为什么说“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里很关键的问题是,中共中央认为应该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但毛泽东认为争取群众与建立政权的过程应同时进行,或者说没有建立政权就难以争取群众,只有建立了政权才能真正争取到群众,建立政权是最大的抓手。当然,建立政权要靠枪杆子,武装夺取政权,并且武装割据。毛泽东认为这样的策略,是可行的,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情的。这个实情就是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分别拥有势力范围。正因此,中国共产党才可以建立根据地政权,即“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块。”[13]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不仅对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有准确的预判,把握先机并争取主动,而且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奥秘也能洞察秋毫。他提及“地方的农业经济”时特地指出“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如果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地方的农业经济就会衰落,从而失去自主性,也就无法支撑必定遭受经济封锁的“国中之国”,即根据地政权。可以说,“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不仅造成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隙地”,也带来中国经济版图上的“隙地”(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以红色政权(根据地)才可以存活下来。朱毛红军当年集结于井冈山,表面上看类似于中国历史上起于“隙地”的义军;但全然不同的是,历史上的义军起于“隙地”之后便忙于一路征讨攻城略地去了,唯有毛泽东带领红军投身于“隙地”经略。可以说,毛泽东最为看重的并非割据地盘的大小,而是在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党和军队是否深入参与其中,并得到锤炼与壮大。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之所以能够胸有千军万马指挥若定举重若轻,就在于他并不看重地盘一时得失(除非时空上的战略要地),而是充分自信于其亲手缔造的党和军队。
事实上,关于打游击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不仅当时的中共中央,而且红军中的不少人都倾向于打游击。中共中央是为了急于求成,而红军中的一些人是为了避重就轻。1929年12月28~29日,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指出,“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14]由于红军中游民的成分很大,所以红军中很多人不愿意去做建立根据地的事情,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而且不愿意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
毛泽东的主张是,红军的成长应该从地方赤卫队开始,然后到地方红军,再到主力红军。他不喜欢搞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事情,一旦这样,红军就成了脱离群众、脱离地方的纯粹武夫。毛泽东认为一定要从地方上、从群众中逐步扩大红军,这样,扩大红军的过程也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党的组织的过程。没有孤立的建军,建军是寓于建政、建党之中的。他说,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会极大地妨碍红军执行正确的任务。那么,什么是红军应该执行的正确的任务?红军不是一般的武装集团,更不能与历史上流寇式的义军为伍,“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5]。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红军的行动便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武装割据而形成的根据地也不是单纯的军事镇守。根据地首先需要“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有恃而不恐”,“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如果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等地方工作没有做好,这个“中心区域”就无“坚实基础”可言。在这个中心区域里,军民必须融合,因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16]。也就是说,红军必须深度介入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等一系列的地方工作。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强调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但并非固守“土围子”;他反对冒进,但绝非按兵不动,而是主张“波浪式”推进。他说:“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17]从井冈山根据地到中央苏区的创建,毛泽东遵循“波浪式发展”的路径,并将之概括为“朱德毛泽东式”路线。他说:“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18]
我们看到这个“波浪式”发展的过程,先是武装割据,集中兵力应付敌人,接着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土地革命这个撬点,把建设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统一起来。即便分兵去开展地方工作,也要注意不能分得太散,否则不利于“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从集中兵力到分兵,又从分兵到集中兵力,割据区域不断扩大、土地革命深入、地方苏维埃政权推广、红军和党的力量的壮大都在同一过程中实现。红军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多重角色,必须极为熟悉地方社会各种情况,所以,红军发展壮大的路径也必须从乡、区、县赤卫队到地方红军到正规红军。如果靠“招兵买马”,则完全有可能征集到与地方社会脱节的兵源,无法在地方开展群众工作。“朱德毛泽东式”根据地的这个发展经验后来也被中共共同前委形象地称为“伴着发展”。1930年3月18日,中共共同前委发布关于分兵争取群众及工作路线的通告,总结了赣南、闽西“武装割据”的新经验,提出了“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通告指出,“分兵游击的意义,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并强调“我们要反对绝对集中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分兵主义”。所谓“伴着发展”,就是伴着原有红色区域发展,“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时间,在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在该区域做深入的工作。“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的具体做法是:第一,分土豪的谷物给农民,以发动群众;第二,进行文字宣传、口头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讲演,以宣传群众;第三,建立工会、农会及革命委员会,以组织群众;第四,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办群众领袖训练班、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有一周或10天工作时间,便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19]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既不是打游击,也不是单纯集中兵力固守中心区域,而是以中心区域为基盘,近距离分兵,围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领导群众、训练群众,同时完成建立地方党组织、建军(赤卫队-地方红军-中央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伴着发展”(党政军相辅相成)、“波浪式发展”、“同时扩大同时深入”(以“三建合一”深入并扩大),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中的“三建合一”的形象描述。
中国共产党、红军、苏维埃政权与根据地人民是充分融合在一起的,苏维埃政权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充分发动、组织、武装群众的结果,地方党组织和军队也同时得以壮大,这样不仅党政分不开、军政分不开,“国家”(政权)与“社会”(民众)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套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或者诸如“政党政治”“军队国家化”等概念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以及今日之党政军,可谓方凿圆枘,全然脱离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人民政权“三建合一”的历史过程、历史事实,无视在“三建合一”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人民政权与西方政党、军队及政权之区别。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拥有深厚社会基础和强大生命力的领导党,其奥秘源于“三建合一”;苏维埃政权之所以不是吞噬社会的怪物,而是激发人民主体性的新生政治力量,其奥秘源于“三建合一”;红军之所以不是一支纯粹的武装力量,其奥秘也源于“三建合一”。
顺便说一句,在今天声称做革命史研究的学者中,有部分人也许还停留在社会史研究的层面,主要关注革命的过激行为如何中断了传统或者偏离了社会常态,他们所利用的素材大多是一些当事人的书信、日记、悔过检讨书、回忆录等边角料。如果真正从社会革命的视野来研究中国革命史[20],必须通过阅读革命经典看到中国革命的“四梁八柱”,我觉得“三建合一”就是中国革命的“四梁八柱”之一。革命史的研究也是需要“经史子集”意识的,如果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史,连《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里的重要篇章都不愿深入研读并细加引用,的确匪夷所思。对这样一种研究,说其“离经”,恐不为过吧。
注释
[1]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8页。
[2]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请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7页。
[3]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
[4]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431页。
[5] [9]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2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1页;第506页。
[6] 《与鲍罗廷等的谈话》,1924年1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2页。
[7] 《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1924年2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5~506页。
[8] 《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1923年1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7页。
[10]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2页。
[11] [16] [17] 《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第94页;第86页。
[12] [1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98页;第97~98、103~104页。
[13]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页。
[14] [15]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第86页。
[1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0页。
[20] 吴重庆:《迈向社会革命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5期,原标题为《“三建合一”的中国革命道路》。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大家都在看
-
战国第一名将白起:一生未尝败绩的军事奇才与背后秘密 引言在中国古代战史长河中,白起的名字如雷贯耳,被誉为“战国第一名将”。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无敌的战绩,赢得了“战神”的美誉。然而,令人惊叹的是,白起一生几乎未曾遭遇败绩,究竟是什么让他成为战国时期最令 ... 军事之最12-20
-
前苏联的军事实力有多强大?一段历史的辉煌与遗产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之一,前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其辉煌的几十年间,凭借庞大的军事力量,成为全球军事强国的代表。其军事实力不仅体现在庞大的兵力和先进的武器装备,更在于其战略思想、 ... 军事之最12-20
-
我国最顶尖的军事武器全解 我国顶尖军事武器以战略威慑、全域攻防、体系作战为核心,覆盖核打击、空天、海上、陆地等全维度,以下为最具代表性的国之重器,兼具技术顶尖与实战威慑力。 一、战略核威慑核心:巨浪 - 3 潜射洲际导弹 1、 地位: ... 军事之最12-20
-
胯下之辱到兵仙传奇!韩信:被时代辜负的军事天才,到底有多可怕 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出身贫寒、受尽屈辱,却凭借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助刘邦一统天下;他功高盖世、战无不胜,却被自己效忠的君主猜忌诛杀。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冠以“兵仙”之称的军 ... 军事之最12-20
-
“飞将军”李广:西汉第一流军事明星的荣耀与悲歌 夜幕下,一支轻骑突然出现在匈奴大营前,箭无虚发,匈奴兵将抱头鼠窜。为首将领弯弓搭箭,箭矢破空之声在草原上回荡——“这就是大汉飞将军!”公元前129年,雁门关外风雪弥漫。四路汉军分道出击匈奴,其中一路由卫 ... 军事之最12-18
-
曹操的三味刀剑:以生平战役讲述军事天才、霸气与诙谐 在乱世烽烟之中,曹操像同时握着三把锋利的刀:一把专攻战局的军事天才之刃,一把压阵的霸气之刃,一把能把紧张气氛拧成轻松笑意的诙谐之刃。他不是简单的战争机器,而是把这三味刀剑交替挥动、互相补充,才在动荡中 ... 军事之最12-18
-
锁钥之地:星星峡与近代西北的权力、贸易与军事通道 在中国西北浩瀚的戈壁与雄峻的天山之间,星星峡如同大地精心设置的一把巨锁,扼守着新疆与内地往来的咽喉。它不仅是地理的分界,更是近代百年来权力角逐、商路转换与军事行动的焦点。一部星星峡的近代变迁史,便是理 ... 军事之最12-17
-
鸳鸯阵破倭巢:戚继光军事智慧的划时代革新 一、卫所制崩坏下的军事革命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股仅53人的倭寇小队从浙江绍兴登陆,竟如入无人之境,直捣南京城下,杀伤明军数千人。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战役,暴露了明朝卫所制度的致命弊端——世袭军户多为 ... 军事之最12-17
-
韩信:从布衣到兵仙的传奇人生,揭秘西汉最耀眼的军事奇才!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军事天才,他的名字响彻千古——韩信。作为西汉初期的杰出统帅,韩信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非凡的军事才能,从一个普通布衣,成长为一代兵仙,影响深远。他的故事,既是一个关于天赋与 ... 军事之最12-17
-
朱能是朱棣靖难之胜最重要的将领之一! 朱元璋能够夺取天下,军事上仰赖的是帝国双壁,徐达和常遇春,而朱棣之所以能造反成功,军事上也仰赖他的靖难双壁,张玉(上篇)和朱能。朱能,字士弘,安徽怀远人,父亲朱亮是朱元璋的旧部,官至燕山护卫副千户。洪 ... 军事之最12-16
相关文章
- 韩信:从布衣到兵仙的传奇人生,揭秘西汉最耀眼的军事奇才!
- 朱能是朱棣靖难之胜最重要的将领之一!
- 二战欧洲战场,为何经济战成为军事打击的最基础作战部分?
- 十年防线被打穿?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俄军对顿巴斯的向往?
- 戚家军不是传说是教科书级的军事现代化实践:被低估的明朝战略家
- 史上最牛的兵家奇才!韩信:从草根到兵圣的逆袭人生
- 刻薄寡恩的军事天才:吴起为何总能成功,又为何总是失败?
- 世界军事史上最经典的合围战之一,斯大林格勒苏军“天王星行动”
- 超级战神:历史上的十大军事天才
- 胯下受辱无人识,登坛拜将三军跪迎!韩信中国史上最悲壮军事天才
- 5艘航母云集中国近海,中美日巅峰对决,美媒:解放军最强最先进
- 千古奇才伍子胥:一代兵圣的军事智慧揭秘!
- 兵仙陨落:韩信的三重悲剧与不朽军事遗产
- 戚继光不但是“抗倭英雄”,还是明朝最卷的“军事产品经理
- 韩信为何被称“兵仙”?他创下3个千古奇功,后世名将难及
- 孙武,兵圣的智慧之光,穿越千年的军事思想巨擘
- 韩信:从草根到兵圣的传奇人生、军事天才的崛起与沉浮
- 普京智囊做出预言:下一个爆发战争的地方既不是台海,也不是南海
- 我军中能够称为“军事天才”的,除了毛主席,还有3个人!
- 曹操:乱世枭雄的铁血与柔情,揭秘三国最真实的“治世之能臣”!
热门阅读
-
战区司令秦伟江 砸店事件背后的真相 07-14
-
南斯拉夫战争始末,强奸妇女惨无人道 07-14
-
98印尼排华,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印尼华人暴乱 07-14
-
高燕生的父亲是高岗,曾与习仲勋是共患难的战友 07-14
-
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最终绑在树上折磨致死 07-14
-
国共内战爆发的最根本原因 中共又为何取得胜利? 05-08
-
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十个超级炸弹,仅次于核弹了 07-22
-
世界最厉害的导弹排名,北星之光位居榜首 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