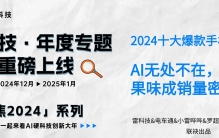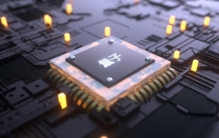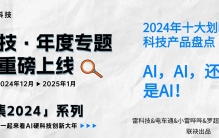诺奖得主:如果评估不合格,我也得离开
文| 孙滔
从4月初约访这位诺奖得主到实现采访,足足过去了77天。
最初的打算是希望他在4月25日前谈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现70周年。可他太忙了。
保罗·纳斯(Paul Nurse)是谈论弗朗西斯·克里克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他是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首任所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希望纳斯来谈谈他眼中的英国科学,毕竟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英国科学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之所以熟悉是在于,牛顿、达尔文、克里克和霍金在中国深入人心;而陌生在于,我们对英国科学今天的认识似乎是模糊的。
英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崇的群体免疫让世人关注,他们的科学家用数据建模来推演疫情成为了其抗疫标签;英国对超级大国有执念,然而约翰逊政府发起的雄心勃勃的超级科技大国计划遭遇了挑战。
中国科学的发展让纳斯印象深刻。明年他将来到中国,集中访问北京、上海和香港。他说,“众所周知,政治可能是复杂的,我们可以依靠科学来改善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很重要,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它很关键。”

保罗·纳斯。图片来源: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中国科学报》:在中国会有一些DNA双螺旋结构发现70周年的讨论,英国有什么纪念活动吗?还有,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
纳斯:我不太确定(英国的庆祝)计划是什么,但庆祝活动会在剑桥和伦敦进行,因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主要在伦敦国王学院,而DNA双螺旋结构的解读是在剑桥大学。两三周之前,我参与了一档科学类电台节目来庆祝。
至于DNA双螺旋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我的看法只能代表个人。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英国有3项重大发现,其一是18世纪牛顿的运动定律,其二是19世纪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进化论,其三是20世纪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这3个伟大发现差不多每100年一个,我认为是英国科学的一大步。后两者属于生命科学领域,与遗传学和进化有关。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是3项发生在英国的伟大发现中的一个,是全世界公认的。
《中国科学报》:请谈谈你和克里克的故事。
纳斯: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是我创建的,也是欧洲最大的医学研究所,有1500个科学家。它以弗朗西斯·克里克命名,而克里克可能是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
我一生都特别尊重克里克。在他们DNA双螺旋结构发现的那年,我才4岁,当我求学期间,他已经是一个传奇。但我对其了解不多,因为他搬到了美国(编者注:克里克于1970年代搬到了加州索尔克研究所)。不过后来在我访问美国以及他返回英国的时候,我们见过很多次。我还邀请他来我管理的研究所做了多次演讲。
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点傲慢和野心勃勃,但晚年之际他在我眼里很有风度,彬彬有礼得更像是传统的英国绅士。他非常有才华,会全面看待问题,并同时从实验和理论角度去理解和研究某个问题。他的思考就像一道激光,那些问题会随着这激光般的思考而消融。
至于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这里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70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实际上我们正在寻求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的主要研究机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也许我们可以交换学生和博士后。我计划明年访问中国,希望能实现这个目的。
《中国科学报》:希望明年能在北京见到你。你能谈谈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吗?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什么?
纳斯:跟多数研究所和大学不一样,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吸纳了各地好的经验。
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的1500名科学家和120个研究小组没有部门之分,没有像细胞生物学、遗传学之类学术院系之分,那么学术兴趣之间的沟通就很少障碍,也没有各个部门负责人去争夺资源或奖项。
第二个不同是,我们向整个生命科学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开放,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对于每个研究小组组长职位,有超过400人来申请,这个竞争激烈程度超过我见过的任何其它地方;对于每个博士研究生位置的申请有多达三四十人。这意味着我们的标准非常高,因此我们可以找到最优秀的人才。
第三个不同是,我不会让每个研究小组变得庞大不堪,而是控制在5人到10人之间,不会到二三十人,这样组长可以照顾好他们的学生和博士后,紧密跟踪实验台上的研究。
最后,我们每过若干年就要对每个小组评估一次,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不合格就要离开,我们这里没有混日子的枯木。
《中国科学报》:我们注意到,新冠疫情期间,英国科学家偏好群体免疫理论和数学模型来应对,这是英国科学的重要标签吗?
纳斯:对于英国科学,我们会说它是经验主义的,非常经验主义的。我解释一下就是,英国科学与数据、观察和事实的联系非常紧密。这意味着我们倾向于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方法,所以新冠疫情期间产生了大量关于疾病传播的数据和出色的分析。你问我英国科学的特点,我认为英国的科学传统是信奉实验,信奉数据,而不是空谈。
《中国科学报》:英国近些年一直在推“超级科技大国”,英国人是不是对这样的计划特别推崇呢?
纳斯:这是一个宏图。我不确定我们的政府是否已经制定了这个宏大的计划,而政府要我做一份关于如何让英国科学发挥作用的报告,我刚刚把它提交给政府,并在其中提出了许多建议。
我们确实需要改进我们的工作,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需要切实可行的方式来提供这笔资金,而之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说,人类社会的大多数进步在某种程度上都基于科学、健康和新技术,基于对世界文化新的理解,基于对科学影响的理解。
我对此举双手赞同,但我们还没有一个好的计划来实现这个目标,希望在未来几年会有改进。
《中国科学报》:这不仅与钱有关,也与文化有关。
纳斯:的确如此。钱确实很重要,我们需要钱,因为政府支出的某些方面已经接近谷底,但我们也需要以适当的方式将资金提供给合适的人。
《中国科学报》:英国有牛顿、达尔文、霍金和克里克,所以他们是超级科学大国的基础所在。
纳斯:是的,作为一个(人口)小国,我们经常赢得诺贝尔奖,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这方面很有效率,我们只需要做得更好。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影响,尤其是ChatGPT的影响?
纳斯:我对机器学习很感兴趣,谷歌的DeepMind是我们的邻居,所以我熟悉这种思维方式,但对教育不太熟悉,因为我所在的机构不做任何教育的事情而只是研究。
我认为机器学习可以帮助发现事物是如何运作的,它可以帮助你找到最需要思考的数据。而ChatGPT会对教育等事情有影响,但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它所做的只是在互联网上搜索所有单词并以特定方式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而互联网上并非所有内容都是合理的,并非所有内容都是连贯的,你永远不会靠它有新的发现。
所以从教育研究的角度来看,使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们将精力集中在思考正确的问题上,但仍然需要大量的想象力来分析、理解并产生思想。
《中国科学报》:你对未来人工智能有担忧吗?
纳斯:很多人确实担心它,如果我们只是任由公司来开发就会像社交媒体一样失控,我认为只要我们是明智的,只要它得到适当的监管(就够了),因为它是一种新生事物,但我并不害怕它。
《中国科学报》:我们希望你多谈谈中国,关于中国的科学和教育。
纳斯:因为疫情,我去中国的计划中断了一段时间。明年我将去北京、上海和香港,这也是我访问中国的集中地。中国科学的发展在我的一生中确实印象深刻。
众所周知,政治可能是复杂的,我们可以依靠科学来改善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很重要,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它很关键。
关于保罗·纳斯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保罗·纳斯,英国细胞生物学家和生物化学家。1949年出生于英国,1973年毕业于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曾于2010年到2015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并曾任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伦敦实验室主任、牛津大学微生物学教授、英国癌症研究基金会主席、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等职务。
他因发现并阐明了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CDK)对细胞周期的关键调控机制,与美国科学家利兰·哈特韦尔、英国科学家蒂姆·亨特共同获得20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于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位于伦敦,由医学研究委员会、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惠康、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合作建设,于2007年启动,在2017年全面开始运营,拥有2000多人和100多个研究小组。
大家都在看
-
最新消息 12月21日凌晨5点前, “德阳造”获“世界之最”科技成果 编辑丨核桃您的点赞关注是我最大的动力!今天是12月21日,星期六,今日精彩要闻有:1、“德阳造”获“世界之最”科技成果认定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2024年重型机械“世界之最”科技成果认定结果,国机重装研制的1 ... 科技之最12-21
-
东菱振动项目获“重型机械世界之最科技成果”认定 近日,根据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的《2024年重型机械世界之最科技成果认定结果的公告》,苏高新股份下属东菱振动自主研制的“1000kN电动振动试验台”被认定为“世界单体推力最大的电动振动试验台(1000kN)”。此次 ... 科技之最12-19
-
地球之最科技篇:世界上最早的自行车 1791年,法国人西夫拉克用木头制造出一辆由横梁连接着的、前后有两个轮子的“木马轮”。1816年,德国人德莱斯在这种木马轮上加了车座和车把,这样在行进过程中便可以改变方向。不久,这种最原始的自行车便在欧洲的上 ... 科技之最12-16
-
“德阳造”获“世界之最”科技成果认定 【来源:德阳日报】近日,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2024年重型机械“世界之最”科技成果认定结果,国机重装研制的13.5米直径圆筒形炼钢烟气电除尘器被认定为“世界最大直径圆筒形炼钢烟气电除尘器”。该除尘装备可确 ... 科技之最12-16
-
中国六大黑科技,个个领先全球,厉害了我的国 中国六大黑科技,个个领先全球,世界为之震撼,国人为之自豪,为我的国点赞。一,华为5G技木:在5G相关技术上,BBC报道称:全球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乃全球5G领先的科技公司,然而这一技术西方国家已落后 ... 科技之最12-15
-
华为Mate XT领衔!2024年十大爆款手机:个个都凶残 2024年,AI硬科技创新大年。“不卷参数卷应用”成AI行业共识。一边,硬件狂叠AI的buff,AI硬件爆发,手机、PC、家电、汽车、清洁、家居、耳机、相机、存储等行业争相妙用AI;另一边,AI深入改造软件,文小言、豆包等 ... 科技之最12-14
-
重型机械“世界之最”科技成果公布 国机重装上榜 中新网四川新闻12月13日电 (李永辉)近日,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了2024年重型机械“世界之最”科技成果认定结果,国机重装研制的13.5米直径圆筒形炼钢烟气电除尘器被认定为“世界最大直径圆筒形炼钢烟气电除尘器 ... 科技之最12-14
-
一夜暴涨8120亿,美国巨头量子芯片划时代突破,中国进展令我意外 谷歌最近发布了一款名为“Willow”的量子计算芯片,通过这款芯片,谷歌实现了计算性能和纠错能力上的重大突破,划时代的进展。这款芯片最新发布后,谷歌市值瞬间上涨8120亿元,吸引全球科技界的目光。报告中提到,该 ... 科技之最12-13
-
2024年十大划时代科技产品盘点:AI,AI,还是AI! 2024年,AI硬科技创新大年。“不卷参数卷应用”成AI行业共识。一边,硬件狂叠AI的buff,AI硬件爆发,手机、PC、家电、汽车、清洁、家居、耳机、相机、存储等行业争相妙用AI;另一边,AI深入改造软件,文小言、豆包等 ... 科技之最12-13
-
世界最大调水工程藏着哪些“科技密码”? 自古以来,我国的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怎么打破这个困境?一项“世纪工程”——南水北调应运而生。南水北调是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也是 ... 科技之最12-12
相关文章
- 精工科技为何火出圈?公司董事长解密背后的新质生产力
- 官方认定!中信智造新添两项“世界之最科技成果”
- 精工科技为何能火出圈?董事长接受专访,解密背后的新质生产力
- 江门中微子实验领先美国5年,中国院士:做第一最重要,老二啥也不是
- “有史以来最具标志性的100项科技发明”是一份您将为之奋斗名单
- 其实,科学也可以很有趣
- 7个惊人的科学事实,一个比一个不可思议
- 钱学森:民族脊梁,科技之光,照亮前行的路
- 科学之城闪耀人才之光
- 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兵器……二里头诞生了10个“中国之最”
- 科学史上最经典的大力出奇迹,莫过于用“土法制冷”挑战绝对零度
- “格美”致资兴受灾十个之最
- 这类化学实验走红!科学之美并非遥不可及
- 快手科技:科技向善,逐梦星河
- 全球最先进导弹大赏:军事科技的璀璨星光
- 肃然起敬,中国近代最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堪称国之瑰宝
- 山东博物馆馆长解锁最薄处仅0.2毫米的“黑科技” :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作
- 世界上最名贵的珠宝,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 华为Mate70,科技巅峰之作,究竟有多先进?
- 探秘奢华之巅:世界上最豪华的游艇,堪称行走的宫殿
热门阅读
-
万事胜意不能乱说的原因?告诉你万事胜意该对谁说 12-09
-
科威特第纳尔为什么那么值钱?比美元值钱的货币盘点 12-22
-
撕心裂肺十大催泪情歌,10首哭到崩溃的歌曲 12-24
-
不敢公布马航真实原因,内幕曝光简直太惊人! 12-25
-
陈百强什么原因怎么走的,陈百强85事件是什么 01-05
-
麻将公式一定要背下来,麻将手气背转运小妙招 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