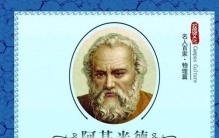不可不读的硅谷创新简史,聊透科技创新核心经验

30亿部智能手机。20亿个社交媒体用户。2家资产达到万亿美元的公司。旧金山最高的摩天大楼。西雅图最大的用人企业。地球上最昂贵的4处公司园区。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一群人。
美国最大的几家高科技公司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最后几年中取得的成就令人难以想象。所谓的科技界五巨头——苹果、亚马逊、脸书、谷歌以及微软——的估值加起来甚至超过了英国的经济总量。这些科技巨头收购知名的传统媒体品牌,给慈善事业带去变革,甚至开始进行登月计划。数十年来,它们自称怯于涉足高层政治,但在西海岸的小隔间中写出的那一行行优雅的代码,早已渗入政治系统的每一个角落。这些代码引发着政治分歧,就像精准投放的在线广告一样有效。[1]
1971年初,当一名从事商业报道的记者给当地冠上“硅谷”这个巧妙的外号时,并没有什么人听说过这个地方以及它周围集聚的电子企业。美国的制造业中心、金融中心与政治中心远在5000千米之外的另一侧海岸。波士顿无论在融资规模、市场占有率还是媒体关注度上,都远超加利福尼亚州北部。
即使10年之后,当个人计算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办公桌上,名为乔布斯或者盖茨的天才少年企业家令公众浮想联翩时,这座山谷本身仍未进入主流视线。当山谷里吹起逆风的时候,硅谷整齐的住宅区总会飘着一层赭色烟雾,使那些色彩鲜艳的办公楼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区分。当地的餐馆在晚上8点30分之后就停止营业了。一名被吓坏了的英国造访者将这里称为“涤纶霍比特人之地”。[2]
“霍比特人”留了下来,只是不再那么慵懒。在“.com”的20世纪90年代,硅谷和它同为科技中心的姐妹城市西雅图扶摇直上,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我们在地球上见过的数额最大的单笔财富积累。”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笑谈道。但在千禧年的黎明,随着纳斯达克遭受重挫,这一切都跌落尘埃,只剩下随处可见的曾经光鲜亮丽的互联网公司的残骸。杂志的封面故事宣告着热潮的结束,面色阴沉的数据分析师把“买入”调整成了“卖出”,华尔街的注意力也转移到了节奏更加容易预测的蓝筹股上。亚马逊火箭般崛起的历程现在看起来仿佛是一场迷梦,苹果的产品创意所剩无几,微软被要求拆分,而谷歌那时还在车库里开展业务,它的领导人更感兴趣的是去参加火人节,而不是如何营利。[3]
一切变化得如此之快。我们快进到现在,硅谷已经不仅仅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个地名。它建成了全球化的网络,成了一个商业敏感点,变成了文化印记,甚至还是一股推动政治的力量。全球有数百个地名被改成了硅漠、硅林、硅湾、硅原或者硅河谷,只为能沾上一点硅谷的魔力。硅谷的律动决定了其他行业如何运作,改变了人们通信、学习与全面动员的方式。它颠覆了许多领域的权力结构,又强化了另外一些权力。正如从硅谷发家的亿万富翁马克·安德里森几年后所说,“软件正在吞噬世界”。[4]
本书讲述的就是世界是如何逐渐被软件吞噬的。这是一段长达70年的传奇,讲述了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个青翠的小山谷如何破解商业成功的密码,以及那里的人如何一次又一次顶住“硅谷已死”的草率传言,发展出一代又一代的新技术,使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试图复制却无法重现他们的成功。这也是一段现代美国的历史:关于政治分歧与大众行为,关于巨大的机遇与令人窒息的歧视感,关于倒闭的工厂与人头攒动的交易大厅,关于华盛顿的大理石厅堂与华尔街的“混凝土峡谷”。正如你将读到的,正是这些因素与其他许多因素一起使硅谷成为可能,同时也反过来被硅谷重塑。
从硅谷闯入公众视野的那一刻起,它就充满了革命性与反体制的内涵。“开始你自己的革命——用你的个人计算机。”1978年创刊的《个人计算机》杂志上的广告这么写道。“个人计算机代表了美国革命留下的最后遗产,即创业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这个大陆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1980年科技期刊《信息世界》如是宣称。
4年之后,当新的麦金塔电脑问世时,苹果公司的高层在营销广告中强调“该产品的激进设计与革命性”,结果造就了史上最有名的电视广告之一。1984年“超级碗”比赛期间,这段令人目瞪口呆的广告在数百万个美国家庭的客厅中播放。广告中一名年轻的女子轻快地跑过一大群观众,将一把铁锤抛向蓝色屏幕上出现的“老大哥”图像,把它砸得粉碎。[5]
这则广告几乎毫不掩饰地针对苹果公司的竞争对手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它超越了营销计划与广告标语本身,在科技行业语境中更多地体现出反体制的意味。“不信任权威——推动去中心化。”在记者史蒂文·莱维描述那些参与实现个人计算革命的软硬件极客的“黑客伦理”中就有这么一条纲领。在这里,“权威”指的是“蓝巨人”、大型企业与庞大的政府。
这条纲领恰如其分。十多年惨淡悲观的商业新闻——工厂关闭、海外蓝领工作机会减少、企业高层四处碰壁以及外国竞争者对美国品牌的沉重打击——之后,光明而充满希望的高科技公司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高科技公司里没有疲惫的经理与满腹牢骚的工人,只有天腾电脑公司的詹姆斯·“吉米T”·特雷比格这样光鲜亮丽的高管,他每周为员工们举办啤酒派对,还在公司游泳池边举行露天新闻发布会。也有高级微设备公司(AMD)的杰里·桑德斯这样的首席执行官(CEO),他买了一辆劳斯莱斯,一周之后又买了一辆顶级梅赛德斯-奔驰。当然,还有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和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他们后来成了新一代企业领导者的典范:年轻、不墨守成规,而且十分富有。
然后那个为时代命名的人出现了——罗纳德·里根,他是反对大政府的斗士、自由市场的捍卫者、他自己所谓的“创业者的10年”的旗手。在这位伟大的布道者看来,没有哪个地方或行业能比硅谷更有代表性地展现自由的美国企业是如何运作的。他也尤其热衷于向国外听众夸耀硅谷的美好。
在1988年对苏联进行历史性访问——这是14年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苏联,而由里根这样一位几年前还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的领导人访问苏联,更是令人震惊——期间,里根面对莫斯科国立大学600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大学生夸耀美国生产的芯片有多么伟大。里根站在列宁的大型雕塑前对人群说,这些高科技奇迹正是美式民主所取得的成果的最佳体现。思想与信息的自由使创新能够涌现,最终产生了计算机芯片与个人计算机。美式自由企业环境,尤其是里根钟爱的低税率、低监管政策的优越性,在高科技企业家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里根提醒台下的学生们,“他们不比你们年长”。他们从郊区的车库里开始小打小闹,最终成长为取得巨大成功的计算机公司的领导者。
那天,里根在莫斯科说,“下一场革命一定是技术革命”。“这场革命的后果会是平和的,但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世界,瓦解旧有的定见,重塑我们的生活。”而这场革命的引路人将是那些敢于“提出想法,被专家嘲笑,然后见证这些想法在人群中燃起燎原之火”的年轻技术人员。[6]
在这场所谓的“个人计算革命”中,主流人群大多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们的左翼政治主张与里根的保守主义相去甚远。但这些“嬉皮士”与里根在一点上可以达成一致:自由市场是计算机革命的灵魂。[7]
当然,这种关于革命的说法并不新鲜。自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以来,美国的发明家和他们政治上或经济上的赞助人就开始大胆(且富有预见性)地宣告新技术将改变世界。从霍雷肖·阿尔杰到安德鲁·卡耐基再到亨利·福特,政治家和记者们将勇于创新又自食其力的创业者的形象拔高,作为美国人“做能为与应为之事”的楷模。“只有在美国,你才能白手起家成为富豪;只有在美国,人们才会根据你的品行而不是血统来评价你。”在这种背景下,硅谷就是美国高科技革命最新、最典型的代表。
罗纳德·里根说得对。高科技革命只会发生在美国。他和其他人将乔布斯、盖茨、休利特和帕卡德誉为创业英雄的确没错。如果没有这些富有远见且大胆的商业领袖,硅谷绝不可能成功。里根与他的保守派盟友也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过度监管的市场和国有企业是开拓创新的巨大障碍——许多本可能成为“硅谷”的地方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歌颂自由市场、个人创业者和全新经济的奇迹之余,硅谷神话遗漏了一些关于现代科技产业最有趣的事,这些事开创先河,又堪称美国经典。个人创业者虽然有天赋,但并非“牛仔独行侠”,他们的成功是通过与其他人、网络和机构合作而实现的。这其中就包括那些大政府工程,哪怕两党政治领袖都对此予以强烈批评,甚至许多技术领袖对此不是怀疑,就是彻底抱有敌意。从炸弹机(一种游戏)到登月工程,再到互联网的基础知识与其他技术,正是公共支出为科学和技术发明的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动力,也为未来好几代初创企业奠定了基础。
然而,就此将硅谷的存在完全归功于政府,就像认为硅谷完全是自由市场的运行结果一样是一个伪命题。这既不完全是一个大政府的故事,也不单纯是自由市场的故事,而是两者的结合。
正如我们将在书中看到的那样,与美国政府对科技的投资同样重要的是这笔资金是如何间接地在竞争中流动的。正是这种流动方式给了科技界的人们极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定义未来,推进技术可能性的边界,并在此过程中赚取利润。是科学家而非政治家或官僚促进了资金的流动,并规划设计了更强大的计算机、人工智能以及因特网——一个由许多节点构成却不需要控制中枢的通信网络。
政府的慷慨大方也扩展到了军工复合体之外。多项放宽监管、为高科技企业减税的政策在商界的游说下被国会立法通过,计算机软硬件企业及其投资人从中获利尤多,这些都促进了硅谷的进一步发展。在研究与教育方面的持续投入训练并资助了下一代高科技创新者。与此同时,政府的大规模计划与集中规划在政治上日益不受欢迎,这使政治与军方领导人基本不插手行业的发展。虽然有数百万美元的联邦资金在硅谷的血脉中流动,但这一地区聚集的技术企业仍然在不受政府关注的情况下生机勃勃地成长。
这种自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自大型机时代以来,政治家只采取了最轻松的手段对这个行业的数据收集行为进行监管,他们只是大致了解了这个行业的技术,但这个行业的迅猛增长带动了整个国内经济的发展。当政府建设的互联网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向商业活动开放时,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家们一致同意只进行最低程度的监管,在涉及用户隐私的方面很大程度上靠这些公司的自律。这一切最终导致社交媒体和其他平台上的内容与链接迅猛增长。但为互联网制定规则的人并没有考虑到坏人会如何利用这个系统,而设计这些工具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创造物将变得多么强大和有利可图。
这个似曾相识的故事还有一点令人意想不到:高科技革命是集体努力与个人天分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并非技术专家的人也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硅谷的成功来自数以千计充满活力的人才,而不仅仅是那些成为畅销传记与好莱坞电影主角的知名人物。其中有杰出的工程师,还有营销大师、律师、技工与金融家。许多人由此致富,但更多人没有。在北加州这个远离政治金融中心的舒适慵懒的角落,他们创造了一个创业者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这里有新型的商业公司,有特立独行的公司文化,还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古怪想法。这里充满了聪明人,他们大多来自其他地方——比如美国的另一头,或是地球的另一端——并且都愿意把熟悉的环境抛在身后,一头跳进未知的天地。“所有的失败者都来到这里,”一位技术行业的老手曾经惊讶地对我说,“然后就会发生奇迹获得成功。”[8]
硅谷与金融及行政中心——更不用提东海岸那些爬满常春藤的学院殿堂——之间的物理隔阂与地理隔阂既是巨大的优势,又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创意在一个紧密相连的小型社群中涌现,在这里,友谊与信任让人们更愿意承担职业风险,容忍职业上的失败。但在硅谷的小圈子所诞生的年代,工程学与金融的世界被白人男性把持,充满了尖锐的性别对立与种族不平等观念,正是这个小圈子在产品应该实现的价值和可以服务的用户方面限制了整个产业的视野。
短视进一步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在硅谷,工程师主导的文化鼓励对优秀产品与拓展市场的单一甚至近乎痴迷的关注,结果往往导致忽视了其他方面。为什么要浪费时间了解政府机构或者传统行业的运作方式呢?反正你的目标就是为了创造更好的东西来颠覆它们,当你正在创造未来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了解历史呢?
但是,革命现实又一次背离了革命神话。虽然技术带来的“新经济”决心打破桎梏,废除僵化的权力结构,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但它仍与传统经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硅谷的风险投资来自洛克菲勒、惠特尼以及工会养老基金。微处理器驱动着底特律汽车与匹兹堡钢铁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与20世纪80年代的“去工业化”浪潮中,当所有的美国人都在期待着更令人充满希望的经济故事时,老牌媒体与传统政客选择支持科技公司,并把这些公司的领导人打造成了名人。硅谷所取得的成就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战后的大量政府投资的基础之上——从太空竞赛年代的国防合同到大学研究基金,再到公立学校、道路建设与税收制度。在现代美国史上,硅谷并不是主流之外的一段插曲。硅谷自始至终都处于历史的中心。
硅谷传奇是创业者与政府的传奇,也是新兴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传奇,还是富有远见的工程师与成千上万让工程师的创意成为现实的非技术人员的传奇。尽管所有其他的工业化国家都试图以某种方式模仿硅谷的创业炼金术,硅谷的公司也已经将它们的触手伸向全球并且带来破坏性力量,但这仍然是一个只属于美国的故事。硅谷诞生于一个特别幸运的时间与地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了不起的1/4个世纪,在美国西海岸。彼时,巨大的机遇正等待着那些热爱技术、有人脉又具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
[1] Associated Press, “Apple, Amazon, Facebook, Alphabet, and Microsoft are Collectively Worth More Than the Entire Economy of the United Kingdom,” April 27, 2018, https://www .inc.com/associated-press/mindblowing-facts-tech-industry-money-amazon-apple-microsoft-facebook-alphabet.html, archived at https://perma.cc/HY68-RJYG.
[2] Reyner Banham, “Down in the Vale of Chips,” New Society 56, no. 971 (June 25, 1981):532-33.
[3] John Doerr, “The Coach,” interview by John Brockman, 1996, Edge.org, https://www.edge .org/digerati/doerr/, archived at https://perma.cc/9KWX-GLWK.
[4] Marc Andreessen, “Why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0, 2011, C2. Billions of dollars of public investment later, many of the would?be Silicon Some?things have fallen short of original expectations; see Margaret O’Mara, “Silicon Dreams:States, Markets, and the Transnational High- Tech Suburb,” in Making Cities Global: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Urban History, ed. A. K. Sandoval- Strausz and Nancy H. Kwa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7), 17-46.
[5] Chiat/Day, “Macintosh Introductory Advertising Plan FY 1984,” November 1983, Apple Computer Records, Box 14, FF 1, SU.
[6] Ronald Reagan, “Remarks and Question-and- A nswer Session with Students and Faculty at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May 31, 1988, posted by John T. Woolley and Gerhard Peters,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54054.
[7] Steven Levy, 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New York: Anchor Press/Doubleday, 1984); Reagan, “Remarks and Question-and- A nswer Session with Students and Faculty at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Also see Fred Turner,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John Markoff, What the Dormouse Said:How the Sixties Counterculture Shaped the 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 (New York: Pen?guin, 2005); David Kaiser, How the Hippies Saved Physics: Science, Counterculture, and the Quantum Revival (New York: W. W. Norton, 2011).
[8] Guy Kawasaki,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anuary 26, 2015, Menlo Park, Calif.
大家都在看
-
全国五大“国家科学中心”开建4年了,现在发展的怎么样了? 当下高速发展的时代,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以人工智能、大数据、5G 技术等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迭代,科技创新无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也已然成为我国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国际竞争主 ... 科技之最04-09
-
阿基米德:古代科学的巨人,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在古代希腊的阳光下,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他的名字是阿基米德。作为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阿基米德的贡献不仅影响了他的时代,更为后世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阿基米德的 ... 科技之最04-05
-
人物传记系列之——郭永怀:以生命铸就的科技丰碑 序章:星陨长空,精神永驻1968年12月5日凌晨,北京西郊机场的玉米地里,一架坠毁的伊尔-14飞机残骸中,两具焦黑的遗体紧紧相拥。当救援人员奋力分开他们的身躯时,一个保存完好的公文包赫然呈现——里面装着中国第一 ... 科技之最04-04
-
如何跨越“死亡谷”?专家共论科技成果转化破局之道 科学家创业成与败的奥秘、硬科技成果转化如何越过死亡之谷、我国产业人才培养存在哪些短板……在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期间,来自高校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研究机构、专业服务机构及创新企业的顶尖“大脑”们齐聚中关村 ... 科技之最04-01
-
可控核聚变+深海科技,最核心的6家(建议收藏) 可控核聚变搭配深海科技,最关键的6家企业(建议收藏)可控核聚变与深海科技,核心的6家企业在此(建议收藏)可控核聚变及深海科技,必知的6家核心企业(建议收藏)可控核聚变和深海科技,最值得关注的6家企业(建议 ... 科技之最03-31
-
中国的最尖端科技是什么 中国当前最尖端科技涵盖多个领域,要说尖端好多科技都是引领全球的。中国敢说第二那世界上还真没有哪个国家敢说自己是第一,就比如我国的激光技术,超强超短激光:上海张江实验装置实现10拍瓦激光脉冲输出(1拍瓦=1 ... 科技之最03-27
-
茶叶中的科学:2025年最值得收藏的春茶科普指南 江南的春晨总带着几分湿漉,采茶女指尖掠过茶树枝梢,将凝结着晨露的嫩芽轻轻摘下。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暗藏着中国人对时间的精密计算。茶对于中国人而言,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饮品范畴,它早已成为一种文化和精 ... 科技之最03-27
-
黄仁勋:华为是中国最强大的科技公司!美国对华为遏制 “糟透了” 3 月 20 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接受英媒《金融时报》采访时,直言美国对华为的遏制 “搞得很糟糕”。黄仁勋作为全球 AI 芯片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这番表态,可不只是对华为技术实力的简单认可,更像是对美国科技霸 ... 科技之最03-25
-
德媒:杭州致力于成为下一个“科技之都” 参考消息网3月24日报道据德国《商报》网站3月22日报道,原本不为人知的深度求索公司(DeepSeek)凭借其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R1一夜之间在科技界引起轰动。此后,中国掀起了人工智能热。DeepSeek的竞争对手面临巨大压力 ... 科技之最03-25
-
世界上令人震惊的黑科技有哪些?这10项颠覆你的认知! 从深海到太空,从量子计算到生物科技,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破技术边界。以下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黑科技”,不仅颠覆了传统认知,更在悄然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进程。一、仿生科技:让机器“活”过来1. 自 ... 科技之最03-24
相关文章
- 茶叶中的科学:2025年最值得收藏的春茶科普指南
- 人民论坛:“最先进的”与“最基本的”
- 黄仁勋:华为是中国最强大的科技公司!美国对华为遏制 “糟透了”
- 德媒:杭州致力于成为下一个“科技之都”
- 世界上令人震惊的黑科技有哪些?这10项颠覆你的认知!
- 又一世界之最诞生!细数子午工程二期里的电子科技
- 艾萨克·牛顿:科学革命的巨人
- 又一世界之最诞生!子午工程二期通过国家验收
- 体验海尔AWE,科技是最好的网红
- 史蒂芬霍金宇宙间最闪耀的科学之星
- 可视科学:用可视化技术诠释科学之美
- 人民日报任平文章:弄潮儿向涛头立 科技创新的中国答卷
- 关中平原种粮科技感“拉满”
- 中国最赚钱的科技公司大揭秘:谁才是真正的吸金巨兽?
- 阿基米德:古希腊的“科学魔术师”,他的智慧比星辰更璀璨!
- 震撼!这些前沿科技,正悄悄重塑人类未来
- 中国最卷985大学,外号“南方小清华”,遍地科技CEO,食堂有36个
- 2025【量子科技】大爆发!6家核心企业齐亮相,你准备好了吗?
- 全球最先进的导弹有哪些
- 中国芯逆袭!24位精度+200万次/秒采样,华为黑科技打破30年垄断
热门阅读
-
万事胜意不能乱说的原因?告诉你万事胜意该对谁说 12-09
-
科威特第纳尔为什么那么值钱?比美元值钱的货币盘点 12-22
-
撕心裂肺十大催泪情歌,10首哭到崩溃的歌曲 12-24
-
不敢公布马航真实原因,内幕曝光简直太惊人! 12-25
-
陈百强什么原因怎么走的,陈百强85事件是什么 01-05
-
麻将公式一定要背下来,麻将手气背转运小妙招 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