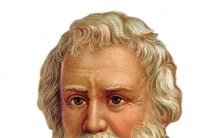人类有“自私基因”,也有“合作”的超能力
文|季东
“合作”这个词,在全球任何地区文化中都不稀奇,一说起来,就会让人联想到坚定的握手和快乐的团队。但合作远不止于此,它早已融入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最无聊的琐事,如早晨的上下班,到最伟大的成就,如将火箭送入太空。英国学者尼古拉·雷哈尼的《人类还能好好合作吗》一书,根据个体、家庭、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再到大型社会的演变,一步步探讨合作是如何进化的。在他看来,合作是我们这个物种的超能力,是人类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几乎在地球上每个地方都能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解决未来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

《人类还能好好合作吗》
[英]尼古拉·雷哈尼 著
胡正飞 译
湛庐文化|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
抚养孩子齐上阵
《人类还能好好合作吗》谈到一个关于合作的令人唏嘘不已的例子。
巴西蚂蚁白天在地面上觅食,但随着夜幕降临,它们会撤退到安全的地下巢穴中。不过,并非全部的蚂蚁都这样做。有几只蚂蚁仍会留在外面,等待它们的同伴全部从一条小隧道爬进巢穴里,然后它们就会开始工作,拖拽、搬运沙粒及其他碎片,从巢穴外面把入口完全隐藏起来。然而,封住巢穴的同时,这些工蚁也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因为落单的蚂蚁在地面上是熬不过一夜的。这几只工蚁如果死在巢穴附近,尸体可能会把捕食者引来。于是,这几只工蚁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沙漠之夜,它们作为尽职尽责的保护者,迎来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巴西蚂蚁的合作行为是出于动物本能,与生俱来,而人类其实也是一样的。人们普遍认为,父母帮助后代是很自然的事。从生物学角度看,这种家族式抚育后代的形式被称为“合作繁殖”。已知的发现表明,两栖动物或爬行动物普遍不会合作繁殖。对昆虫、蜘蛛、哺乳动物和鱼类来说,合作繁殖的比例徘徊在1%甚至更低,而鸟类稍高,也仅有8%。
合作繁殖并不容易,因为合作本身就是有门槛的。如果将合作繁殖物种的分布放到世界地图上,可以发现它们往往集中在一些环境恶劣的地区,如非洲沙漠中的狐獴和鼹鼠,澳大利亚内陆的白眉雀鹛和灰短嘴澳鸦,以及中南美洲的沟嘴犀鹃和棉冠狨猴。
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境况非常相似:先民大部分都生存在这个星球最困难的环境中,每个个体都必须积极寻求赖以生存的食物。这种觅食的生态环境风险很大,因为食物不容易找到,大型猎物也会反击,而且各种觅食技术都需要时间来完善。无论是参加团队协作,还是从他人那里学习技能,都对生存至关重要。
人类是合作繁殖者,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人类社会及其育儿模式很有帮助。在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母亲们都融入了庞大的社交网络中,孩子被多方抚养长大,抚养者包括父亲、哥哥姐姐、阿姨、叔叔以及祖父母。当代的人类社会仍然在以这种模式运作,只不过,“大家庭”在工业化社会中已经被更专业的机构取代,如学校和托育机构等。
人类这种与生俱来的成长环境,对于合作性格的塑造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人们往往不愿意独来独往,更喜欢成群结队,实际上,不仅仅只是因为喜欢,也是因为需要。被排除在社交圈子之外,确实会引发我们大脑中的痛苦信号,就像手烧伤或者骨折的时候大脑发出的信号那样真实。孤独感伴随着一系列潜在的副作用,睡不安稳,免疫功能下降,直至死亡风险增加。
乐于助人是天性
更有甚者,合作会使人快乐,所以我们会乐于帮助他人。
当你为某个人做一件好事时,你所获得的那种模糊的感觉,就如同经济学家所说的“温情效应”,这种感觉也是心理学、社会学所关注的。有研究显示,如果给人们以机会,让他们为慈善事业汇款,同时通过大脑扫描仪检测,就会发现他们大脑中的“奖赏”区域会兴奋起来。这块区域,和人们在享受美食或者沉迷于游戏等娱乐性活动时的大脑活跃区域是一样的。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给了参与者一大笔现金,并指示他们要么自己用,要么用在别人身上。结果发现,到了那天晚上,那些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人感到更加快乐。同一组研究人员还表明,当被要求与玩偶分享饼干时,幼儿的笑容比没有被要求分享时更多。还有,在别人身上花钱,甚至还有助于降血压、改善心血管健康。
那么,为什么人类的大脑中充满着这么多心理机制,驱使着我们做出如此代价不菲的行为呢?《人类还能好好合作吗》认为,促进合作的最简单机制是助人者得人助,也就是互惠原则。这一原则最初由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提出。互通有无、各得其所,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己之所欲、施之与人,善有善报、好人好报……这些格言在许多语言中都能找到同款。放眼全世界,互惠似乎是指导行为的普适准则。
不过,在动物界中互惠原则并不普遍,只有少数物种和人类一样,存在着社会交换的需求。例如,吸血蝙蝠每天都需要一顿血液大餐,不然就活不下去,但有时找到这顿饭是个大麻烦。吸血蝙蝠过着大型聚居的生活,那些成功觅食的蝙蝠经常为当晚未能开荤的倒霉伙伴们反刍。一只蝙蝠在某一天晚上“献血”,另一天晚上就很可能获得受益者的补偿。
其他物种所交换的不是血液,而是某种服务。例如,生活在珊瑚礁上的色彩亮丽的蓝子鱼,它们在觅食的时候会与一个伙伴合作,轮流提防捕食者出现。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来自斑姬鹟,实验表明,这些鸟儿只帮助那些以前为自己出过力的邻居。尽管斑姬鹟是成对繁殖的,它们还是会经常去滋扰那些出现在邻居巢穴附近的捕食者。这可不是小事一桩,帮助邻居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而且还有可能把自己暴露在捕食者的眼皮底下。研究人员针对它们的义举进行了调查,他们把一个假的猫头鹰模型放在一对斑姬鹟的巢穴内,还临时性地诱捕了邻居以阻止它们赶来相助。研究人员发现,几天后,就算是把猫头鹰模型放在那些“背信弃义”的鸟儿的巢穴内,他们所关注的斑姬鹟也已经拒绝向“不仗义”的邻居提供帮助了。
但是,人类就不会那么斤斤计较。在生活中,人类并不拘泥于在每一次社会互动中都患得患失,这其实是向自己的伙伴们传递出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信号,即我们之间相互仰仗,伙伴们不需要在每次交往中都平衡收支,伙伴的利益与自己也休戚相关。“如果纠结于上周你给谁买了杯奶茶,所以现在他应该还回来,那你的格局就太小了,因为这意味着一杯热饮的价格超出了你和他之间的利益关系。这表明,我们也没把咖啡之交当成好朋友。”尼古拉·雷哈尼解释道。
基于此,他提出一个问题。如今,有些应用程序允许朋友们在外出喝酒或者吃饭的时候开出费用清单。这项技术的确消除了AA制拆分账单的麻烦,但这也许又会让人不太自在。细想一下,这种不自在有着充分的理由:我们如此讲究互不相欠,无意之中,是否破坏了我们的社会关系结构?
未来更要超越本能
合作确实是必要的。
威胁、生存和疾病,它们从人类出现以来就与我们朝夕相伴,是真正的人生大害。如果能避免被攻击或伤害,还能获取保证健康所需的食物,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这就是所谓“物质安全”的本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类从根本上需要合作。
尼古拉·雷哈尼指出,合作是一种社会保险形式,万一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合作就是一种缓冲风险的方式。人类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种社会保险是以紧密的社会网络的形式出现的,其中包括朋友和家庭。
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本地的、个人的关系仍然是缓冲生活风险的基本手段。在许多非工业化社会里,人们按照惯例和邻居朋友们分享食物,而分享食物就是一种缓冲生活中起起落落的方式,特别是在人们无法从外部市场买到东西的时候。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利用互相高度依存的关系分散风险,是在严酷恶劣的、不可捉摸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手段,对于许多人来说,直到今天,这种关系仍然是社会保险的主要形式。
然而,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从社会视野看,合作的障碍在于自私所带来的短期利益。例如,一条稀有的、重达270公斤的蓝鳍金枪鱼,在东京的丰洲海鲜市场被卖到310万美金。这是一大笔钱,足以让人背弃原则,特别是如果你相信即便不是你抓住并卖掉它,其他人也会这么做。通过这一切,我们可以意识到,仅凭不冷不热的口号来激发人类更美好的天性,指望这样就可以解决重大问题是多么天真和危险。
我们不禁有些惶恐。对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居民而言,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和未来的人而言,生活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尼古拉·雷哈尼认为,我们的担心是对的,但是不应该因此失去希望。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不同,我们有能力找到摆脱社会困境的方法。天赐游戏,我定规则。人类不只是被游戏所困,还可以改变规则。
在这个领域里有着无数的例子,凸显了人类的聪明才智。无论是采猎者决定如何分肉,儿童们决定轮流使用玩具,还是国民们决定投票选举掌权的政治代表,都是在创建和改变规则,目的就是为了成功协调个人利益,通过合作生产出更多的公共产品。尼古拉·雷哈尼指出,我们需要利用人类的聪明才智来创建有效的制度,制定各种规则、协议和激励措施,这些制度将助长合作与长远的眼光,而不是鼓励自私和短浅的视角。我们可以预见更有效的方案,可以设想更光明的世界,也可以为我们的社会设计章程规则,让人们充满动力地进行合作。
鉴于人类在地球上的巨大存在和非凡影响,我们需要超越本能,打破常规、破旧立新才能别开生面。《人类还能好好合作吗》提到,大多数时候,与亲人合作,或者与已经有关系的人合作,都很容易,但是,要把信心寄托在我们素未谋面的人身上,可就困难得多了,而这正是全球问题需要我们做的事。

大家都在看
-
绝境中的微光: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希望密码 敦煌莫高窟第254窟的壁画上,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穿越千年依然震撼。当王子坠入悬崖的刹那,画家特意在云层中勾勒出若隐若现的佛光——这是绝境中最古老的希望图腾。在切尔诺贝利核废墟中,生物学家发现一种特殊 ... 人类之最03-29
-
人类全身上下最强韧有力的肌肉,竟是舌头? “舌为心之苗”,在中医理论中,舌头被视为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窗口。而在现代科学的视角下,舌头同样有着诸多令人惊叹的特性。关于“人类全身最强韧有力的肌肉是舌头”这一说法,虽然存在一定的误解,但舌头的独特之 ... 人类之最03-28
-
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十大发明!第七个让全球沸腾,你每天离不开它! 从钻木取火到人工智能,人类用智慧点亮了文明的曙光。这些看似普通的发明,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重塑了世界格局!今天,就让我们盘点史上最伟大的十大发明,看看哪些发明让你惊叹不已?1. 车轮(约公元 ... 人类之最03-24
-
人体最强大的能量,都是来自于心神合一、内守灵魂本源 在现代的社会中,我们常见许多人被情绪左右,从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能量。试想,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繁琐的事情或者在生活中面对困境,是不是常常觉得难以集中注意力,甚至陷入无休止的烦恼?而这种情况,大多数时候 ... 人类之最03-24
-
一起来认识一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科学家 人类文明的灯塔:十位科学先驱的永恒光芒在人类文明的漫漫长河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着认知世界的征程。这些科学先驱以智慧为火炬,以探索为舟楫,在时空的维度上镌刻下永恒的精神丰碑。从古希腊的思 ... 人类之最03-21
-
合集•人生感悟之三:人类最珍贵的是真心实意 人真心实意的互相关爱、互相帮助,则人与人之间美好、家庭与家庭之间美好、国家与国家之间美好、人类世界之美好。△共同创建和谐、幸福美好的社会什么是真心实意所谓真心实意(是个成语):指的是心意真实、真诚,毫 ... 人类之最03-14
-
人类极限大赏:生活中那些惊掉下巴的“世界之最”! “你总觉得生活平淡无奇?那是因为你没见过这些‘疯狂’的人类!”当普通人还在为早起打卡、减肥健身发愁时,地球上却有一群人用行动诠释着“极限”二字。有人用62年不剪指甲换来一副“九阴白骨爪”,有人为一口美食 ... 人类之最03-03
-
中国最伟大的人—毛泽东 在人类文明的浩瀚长河中,那些改天换地的英雄人物,如璀璨星辰照亮历史的天空。而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存在。这位从韶山冲走出的农家子弟,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迈气概,踏上了改写中国命运的征程 ... 人类之最03-01
-
陕西深山现身5万年前人类头骨,竟暗藏华夏先祖进化的印记? 题记:在黄土高原的褶皱深处,一段被时光封印了数万年的惊天秘密,正随着考古学家的小刷子层层剥落...一、神秘头骨的惊世现身1983年的深秋,陕西黄龙县尧门河水库的工地上,铁锹与岩石的撞击声突然戛然而止。当民工 ... 人类之最02-26
-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四大哲学家,他们分别是哪四位?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四大哲学家,他们分别是哪四位?在人类思想的长河中,哲学家们以其深邃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智慧财富。在众多杰出的哲学家中,有四位因其思想的深远影响和卓越贡献,被普遍 ... 人类之最02-21
相关文章
- 人类极限大赏:生活中那些惊掉下巴的“世界之最”!
- 中国最伟大的人—毛泽东
- 人类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三大死亡事件,最后一个让人脊背发凉!
- 陕西深山现身5万年前人类头骨,竟暗藏华夏先祖进化的印记?
-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四大哲学家,他们分别是哪四位?
- 世界十大核事故排名:苏联排行第一,日本美国各占一半
- 世界十大食人魔:张永明上榜,第四名凭借吃人在日本混的风生水起
- 史上最漂亮的十大化学实验:人工染料上榜,第十获得诺贝尔奖
- 世界上最好学的五大语言,西班牙语排第一位
- 人类极限的最强数值#世界之最
- 当AI凝视人类:那些算法无法解答的终极之问
- 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四种酷刑,让人毛骨
- 为什么说乾隆是整个人类史上最舒服的帝王?
- 兔子造成人类史上最严重的生物入侵?澳大利亚任命“野兔总管”
- 韩江:去凝视人类最柔软的部分
- 上帝手抖合集,那些人体器官之最!
- 我国首部太空实景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创下人类多个“之最”
- 南京发现世界最早马镫 该马具改变了人类战争史
- 全球最难学习的五大语言:汉语排榜首,冰岛语上榜
- 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五大货币,津巴布韦元排第一位
热门阅读
-
关于男人的15个世界之最,最长阴茎达56厘米 07-13
-
东方女性最标准的乳头(图片),看看自己达标吗 07-13
-
人体器官分布图介绍 五脏六腑的位置都在哪 07-13
-
木马刑是对出轨女性的惩罚 曾是满清十大酷刑之一 07-13
-
熙陵幸小周后图掩盖性暴力 至今保存于台湾博物馆 07-13
-
包头空难堪称国内最惨案件 五名遇难空姐照曝光 07-13
-
2022中国最新百家姓排名,你的姓氏排第几? 03-26
-
好玩的绅士手游有哪些?2022十大绅士游戏排行榜 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