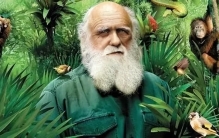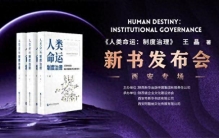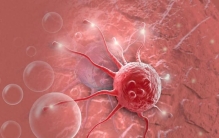探索神秘的大脑神经,带你了解人类那些神奇的特异功能

在历史上,有不少关于人类可以变身成动物,再变回人形的传说。其中最令人生畏的就是狼人了,由于不能控制自身的兽性,它们常常变身为残酷和恐怖的杀手,还会吃活人和生肉。
几乎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期,都有这种人兽转化的故事:从最早的民间传说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潘”,到古罗马神话故事里的莱卡翁。相传莱卡翁是阿卡迪亚残暴的国王,后来因为得罪了宇宙之神朱庇特被变为一匹狼。即使在今天,只要翻几页《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和《暮光之城》(Twilight Saga),你就会发现人们对这些血腥的狼人故事仍然津津乐道。
也许你会好奇狼人跟不可思议的大脑有什么关系。一个惊人的事实是,狼人并非只存在于流行小说和民间传说中,早期的医学文献就记载了人们会变成动物的案例。公元7世纪,在亚历山大行医的保罗斯·艾吉内塔(Paulus Aegineta)认为,这些患者可能具有抑郁质,或者说是黑胆汁分泌过量。到了中世纪时期,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黑法术,甚至是魔鬼让兽人发出野兽般的嚎叫,想吃生肉并攻击其他人类。
那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疾病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时治疗其他症状的某些药膏可能会有副作用,让人一直有刺痛或者针扎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被认为是皮肤里的毛发在生长,就被当成了人变身成动物的“证据”。
某些历史学家提出罪魁祸首可能是食用了某些药用植物,如罂粟花或天仙子——一种类似于有毒颠茄的植物。在17世纪,草药医师会使用天仙子作为镇静剂,治疗风湿性疼痛和牙痛。我们现在知道,这些疗法可以引起逼真的幻觉。很多记载表明,在食用这些草药之后,人们会以为自己变成了豹子、蛇或某种神兽。
后来人们尝试了各种对策,包括饮用醋、放血疗法,还有最夸张的是用银制子弹射击。
最著名的一个狼人案例是在17世纪初期的让·格雷尼尔(Jean Grenie),来自法国朗德省一个14岁的男孩。格雷尼尔吹嘘自己吃了50多个孩子。他说他会用四肢在地上行走并想吃生肉,尤其是小女孩的肉,他声称“很美味”。[1]格雷尼尔最终被判处了绞刑,然后尸体被焚烧。但执行之前,当地的调查机构派去两名医生对他做了检查,他们最后认定格雷尼尔得了“一种被称为变狼狂的病,是一种由邪灵引发的让人妄想的病症”。[2]于是格雷尼尔没有被处决,而是被送到了一个修道院。
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外科医师们定论这不是一种灵异现象,而是一种精神疾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临床变狼狂的定义渐渐变得更为宽泛,病症包括任何变身为动物的妄想。有报道称,有的患者认为自己变成了狗、蛇、鬣狗,甚至是蜜蜂。而这种疾病非常罕见,荷兰帕纳希雅精神病研究中心的精神医师简·德克·布洛姆(Jan Dirk Blom)搜索全球记录,在过去的162年中只有13个被证实的患者妄想自己是狼人的案例。
我对这种不同寻常的病症一方面很好奇,另一方面又感到些许不安。莎朗和鲁本让我认识到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不尽相同,西尔维娅让我了解到人人都能体验到幻觉。但这种病似乎更加夸张: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对自己的人形都不屑一顾的?一个人怎么能相信自己没有手和腿,而长了爪子甚至翅膀?我不禁好奇,对着镜子看到一只野兽正在看着自己是什么感觉?这种病能让我们认识到大脑是如何看待我们躯体的吗?
正如布洛姆的调查显示,临床变狼狂的病例非常少,所以我没有期望能遇上任何患者。不过我还是会不定期地询问专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看看他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病人。很快我就发现,临床变狼狂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往往伴随其他常见精神病一起出现,比如精神分裂症。我接触过的大多数医生都说他们从来没遇到过这种病例,只有一个人,阿联酋大学的医学与健康科学院的院长哈姆迪·莫塞莉(Hamdy Moselhy),接触过这种病例。事实上,他是全世界少数几位不止一次治疗过这种疾病的研究人员之一。
哈姆迪遇到的第一起临床变狼狂病例,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英国伯明翰诸圣医院担任注册员的时候。他在那里见到了一名36岁的男子,他几年前因为在汽车道上徘徊而入院,之后一直表现得很奇怪。这个病人在地上爬行、吠叫,还会吃街上的呕吐物。他对医生说自己是一只狗,还听到声音告诉他要做狗应当做的事情,比如喝厕所马桶的水。[3]
当我第一次和哈姆迪谈话时,他告诉我:“我当时从没听说过还有这种表现的精神病,我以为他可能是犯了罪装成这样来逃避。”他跟他的主管谈了这件事,主管让他去了解一下临床变狼狂。哈姆迪搜索了所有医学文献,如饥似渴地研究过去的那些案例。
他发现有个案例描述了一名34岁的女性。她来到急诊室就诊时非常焦躁不安,突然间她开始像青蛙一样跳来跳去,呱呱叫,伸出舌头好像要抓苍蝇一样。另一个案例描述了一个女人总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蜜蜂,变得越来越小了。[4]
2015年下半年,哈姆迪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他有一个名叫马塔尔(Matar)的病人,这些年反复受到临床变狼狂的困扰,有时连续几个小时他都认为自己真的变成了老虎。但现在他的情况已经得到控制,而且也愿意和我谈这件事。最后他问我:“你要不要来阿布扎比和他见面?”
现在还是早上9点,温度就已经飙到了44℃。坐在舒适的有冷气的出租车里,窗外炫目的摩天大楼一闪而过。远处的地平线上,屹立着巨型棕金色圆顶的谢赫扎耶德大清真寺——阿联酋最大的清真寺。当我们一路向西行驶到城郊时,周围不再是宏伟的建筑,而是一排排破旧的小商店。我们转入一个由棕榈树间隔的宽阔的高速路上,周围的建筑物突然消失了,仿佛进入了一个隐形的边界。两边的景色变成了一片荒芜,只有沙丘、怪树和偶尔的骆驼队。
就在这样的景色中,我们又开了一个小时。
当我看着沙丘出神时,司机艾木哲德突然说道:“艾因当地的村民都是非常淳朴的人。”一下把我从恍惚中唤醒。我环顾四周,注意到旁边的道路多了些绿色。
也许当地人会把自己当成乡下人,但艾因事实上是阿联酋的第四大城市,距阿曼边境不远。由于这里有很多公园和绿树成荫的大道,有时它也被称为花园城市。
沿着某一条街走下去就到了艾因医院,艾木哲德停下车,我一跃而出。像是打开了烤箱一样,空气中的热浪袭来,于是我快步走进眼前的空调大厦里。接待我的是哈姆迪和拉菲亚·拉希姆(Rafia Rahim),一位柔声细语却思维敏捷的专科医生。我们3人往主楼走去,我问拉菲亚马塔尔今天怎么样。
“他身体还好,”她说,“但从早上开始他就一直有点焦躁。”
宽敞的走廊里人来人往,马塔尔就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他穿着传统的阿拉伯长袍(一种长长的白衬衫的传统服装),带着白色头巾。他大概45岁,但眼底的黑眼圈让他显得比实际老一些。他浓厚的黑色胡须已经开始变灰,胖乎乎的脸颊上有不少褶皱。
当哈姆迪热情地向他打招呼时,他从座位上站起来。
“这是海伦。”哈姆迪说。我伸出手,马塔尔轻轻地握了一下。
我们一行穿过医院走到一排空旷的办公区。在走廊尽头是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面有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哈姆迪让我们坐下,自己去拿了一些水。马塔尔选择坐在离门最近的椅子上,而我坐在他的斜对角。拉菲亚留下我们去她的办公室拿东西。
就剩我们两个人时,我对马塔尔微笑致意,感谢他到医院来跟我见面。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就将头转向一边,看上去有些困惑。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似乎没明白我说的话。我知道马塔尔的英语不太好,但我以为他还是能听明白一点点。我微笑着然后向门口的方向点点头。“那咱们就等哈姆迪来吧。”
我俩静静地坐在那里,我回忆着马塔尔的情况。他16岁时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当时,他需要经常在当地的精神病院入院治疗。有一次他打电话告诉警察有人袭击阿联酋,因为当时他出现了炸弹爆炸的幻听和幻视。警方甚至为这通电话派出了军队,后来马塔尔也因为提供虚假情报被捕。
成年后,马塔尔告诉他的医生自己除了经常出现幻觉,有时在夜晚他会变身成老虎。他说能感到自己的手脚上开始长出爪子,而且他会在房间里咆哮。当他变身时会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因为他担心一旦到外面去会吃人。他之前跟哈姆迪讲过。一次他在理发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老虎,他当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试图撕咬他的理发师。
精神分裂症通常被认为是所有人类疾病中最复杂的病症之一。约1%的人群会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常见症状包括偏执、幻觉、思维混乱和缺乏主动性。目前我们仍然不清楚它的具体成因,但遗传因素占有很大比重(患者的直系亲属患有这种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得多),心理创伤和滥用药物等环境因素也是致病的显著诱因。
一些遗传学研究认为,精神分裂症可能是由22号染色体突变所致,其中一段已知区域在神经细胞的发育和成熟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日本理化研究所脑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们从突变人群中获得他们的干细胞,用以培养神经细胞。研究人员发现与没有突变的干细胞相比,突变体产生了较少的神经细胞,而且迁移的距离更短。[5]这个发现说明,突变体可能导致早期的神经系统生长发育异常,从而会影响到大脑各个神经网络之间的交流。
由于精神分裂症的症状非常广泛,我们难以断定是哪部分的神经网络受到的影响最大。但近年来有理论提出,可能是负责区分自我和外界信号的某一部分神经网络受损,导致了疾病的某些症状。
我们通常很少留意这个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本能地就知道伸腿时是自己的腿在移动,或者讲笑话时听到自己说话。但我们之所以能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大脑可以从自身行为来预测出感官刺激,从而让我们感觉到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所说所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伦敦大学学院的克里斯·弗里斯(Chris Frith)和他的同事一直在致力于发展一种理论模型用以阐述这种操控感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用它来解释精神分裂症的某些症状。[6]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你可以试着抖动一下自己的腿。要做出这个动作,你的运动皮层,位于顶部的一个脑区会向腿部的肌肉发出信号让它们前后移动。根据弗里斯的模型,与此同时这个信息的副本也被发送到其他脑区,从而创建了对即将到来的运动的心理表征,也就是说对这个行动的后果做出了预测。一旦你的腿摆动,从腿移动的视觉图像到皮肤肌腱关节摩擦产生的触觉,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感受都会和这个预期做比较。如果二者匹配,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行动产生出操控感。
当大脑处理这些自体感觉时,不会像对外源感受那么敏锐。这种适应性是非常巧妙的设计,因为它意味着当我们碰触自己的手臂时,不会像被别人突然抓住那样吓一大跳。同理,当我们讲话时,大脑会把命令声带运动的指令副本发送到听皮层。在我们说话几百毫秒之后,我们的听皮层就受到了抑制。而当你听到别人说话时,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这表明大脑会根据你的声带运动对发出的语音进行预测,并将其与传入的声音比较。如果二者匹配,声音就会被认为是你自己发出的,然后被适当地忽略掉。
但如果整个系统的任何一部分出现了问题,不论是交流不畅还是时间不匹配,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意图和行为及感官效应进行有效的关联,从而使大脑认为事情的发生另有原因。
2016年,法国里尔大学的安娜—劳尔·勒梅特尔(Anne-Laure Lemaitre)和她的同事们专门验证了这个理论能否解释精神分裂症。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你在家里就可以尝试。你只需要脱掉上衣,把左臂向上伸展开来,然后用右手伸到左腋下给自己挠痒痒。很可能这完全没用——我们很难让自己觉得痒痒。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对右手的后果做出了预测并抑制了对此的反应。感到痒痒的必要条件——悬念和意外感——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当勒梅特尔测试那些精神分裂症状的人群时,他们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这些人更容易感到痒痒。[7]这个结论支持了解释精神分裂症的理论,因为这些患者不能有效地预测自己行为产生的感官效应,有可能导致他们不能区分自身行为产生的感受和外界带来的感受。
另外,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还发现,他们识别预测自己声音的机制也出现了异常,使得大脑无法轻易区分内源和外源的声音。由此不难想象,这些异常也可能让一个人认定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或者内心的独白并非来自本身,而是来自其他地方。
哈姆迪为每个人拿来一小壶水,把我的思绪带了回来。他在我旁边坐下,不久之后拉菲亚也回来了,她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当我感谢马塔尔当天专程来到医院时,哈姆迪帮我翻译了这段话。马塔尔本来没必要来,他平时和妈妈、妹妹住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村庄里。为了和我见面,他特地一个人来到这里。
我问马塔尔他是否愿意给我讲讲他的故事,他长大的地方,他有没有成家。他想了一下就温柔地回答说他有妻子,但他马上又变得犹豫不决。我之前读过变狼狂的患者经常会感到拘谨,所以我转向哈姆迪对他说:“请转告他,如果他不愿意就不需要回答我的问题。”
这时马塔尔突然面部抽搐起来,仰面朝天还发出了怪叫。我一时惊慌失措,片刻之后才意识到他是在哭泣。他仰着头看向天花板,肩膀上下起伏着。拉菲亚拿起一盒纸巾递到桌子对面。马塔尔擦干了泪水并向我道歉。他说自己伤心是因为他还有两个孩子,但自己再也不能去见他们了。他只记得其中一个大概14岁,另一个8岁。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因为自己很长时间没能看到他们了。
他说:“我的妻子不希望他们看到现在的我,她带着他们住在很远的地方。”
哈姆迪转向我解释到,在马塔尔开始出现变狼狂症状之后,他的妻子就带着他们的孩子离开了,因为她认为他可能会伤害到他们。我点点头,虽然不能用语言表达,我试着通过我的行动向他表示同情。
过了一会儿,哈姆迪问马塔尔还愿不愿意继续接受采访。他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于是我接着问他症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还有什么感觉。
他说:“最开始,我的精神分裂症是一些幻视。我看到一些人走来走去,但他们其实并不存在。我能感觉到他们,男人、女人和小孩抓住我的腿,后来我摔倒在地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幻觉愈演愈烈。“我感到那些人开始控制我的谈话,他们能读懂我的思维。他们也不允许我说话。”
突然,马塔尔停了下来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他对哈姆迪说了什么,然后手指朝我的方向虚晃了一下。
我看向哈姆迪。
“他说因为你是英国人,他觉得你很可疑。”
“为什么?”
哈姆迪转向马塔尔让他说说他的理由。“我们说了太多英语,”哈姆迪说,“这让他很焦虑。”
接着他俩用阿拉伯语聊了一会儿,谈完之后马塔尔似乎平静了下来。他说他实际上非常喜欢英国。他告诉我他曾获得了去英国大学的奖学金,但还需要学习英语。他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去英国读书。
他看起来放松了不少,于是我问他能不能说说他当时觉得自己变成老虎时是什么感觉。马塔尔想了一会儿,然后指着自己的头和脖子说:“我能感到自己的头脑和身体都发生了变化。”
他卷起袖子露出自己的手臂,揪了一下自己厚厚的黑色汗毛,让它们竖起来。
“当我感觉要变身时,所有的毛发都会竖起来,全身毛发都竖立起来。然后我感到全身和胡须上都有一种针刺般发痒的感觉。左腿最先感到疼痛,接着是右腿,最后是手臂。然后全身会有一种触电般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想咬人。我完全没法控制自己,只知道自己变成了一只老虎。”
他突然停下来摸摸自己的喉咙,然后直勾勾地看着我说起了阿拉伯语。
我望向哈姆迪,他看起来也十分困惑。“马塔尔说他现在就有这种感觉。”
媒体常常把精神分裂症患者描绘为一些有暴力倾向的人,但事实上,这个指控并没有科学依据。就职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伊丽莎白·麦金蒂(Beth McGinty)和她的同事分析了1995年至2014年的新闻报道,他们发现所有关于精神疾病的新闻报道中,有40%强调了精神病与暴力之间的关联。然而这与实际生活中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率完全不符。
举例来说,在英国,精神障碍相关的凶杀案在1973年达到顶峰,之后一直在稳步下降,到了2004年(分析数据的最后一年)比率为千万分之七。相比之下,同期的凶杀案总数一直在增加,在2004年达到峰值:每1000万人中有150人死亡。[8]
对于公众媒体和法律制定者来说,这种误认为精神病是暴力根源的想法很危险。不可否认的是,精神病确实可以导致暴力,比如闹得沸沸扬扬的暗杀美国政治家加布里·埃尔吉福兹(Gabri-elle Giffords)的行动是由贾里德·李·拉夫纳(Jared Lee Loughner)所为,后来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然而大多数暴力行为并非由精神分裂症的幻觉和偏执所致,而是愤怒和其他情绪问题——吸毒、酗酒的结果。麦金蒂说,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对待他人并没有暴力倾向,而且大部分暴力并非由精神疾病引起。
想到这些,我心安下来。我打算听从哈姆迪和拉菲亚的指示。他们正在低声地和马塔尔说话。他们让他放松下来,在这里大家都是朋友,没必要感到焦虑。
马塔尔似乎正在与身体中的某种力量做斗争,房间安静得像是过了好几分钟。突然间他抓住了自己的双腿。
“你是觉得自己想要攻击别人了吗?”哈姆迪打破了沉默问道。
马塔尔抬起头看着他。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会读心术吗?”
哈姆迪向他保证自己无法读懂他的想法,只是单纯地在询问他的感受。
马塔尔用充满怀疑的眼光看着他,然后用阿拉伯语说了些什么,让哈姆迪笑了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道。
“马塔尔问我是不是他认识那个真正的哈姆迪。他怀疑我可能是个冒牌货,因为他说自己记忆中的哈姆迪很胖。”
马塔尔点了点头。他说:“我认识的哈姆迪非常胖”。
我看着哈姆迪皱了皱眉头。“哈,他是对的,”他微笑着说道,“我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没见到马塔尔了,上次我们见面时我真的很胖。”
哈姆迪向马塔尔解释说他最近瘦了很多,而且马塔尔肯定也认出了他和拉菲亚两个人。
“我认识的哈姆迪更善良。”马塔尔说。
哈姆迪微笑着又和马塔尔聊了一会儿,他问他是要继续还是结束谈话。突然间马塔尔的肩膀完全放松下来,目光也变得更加集中起来。
“好,我们继续吧。”他说。
我深吸一口气,问马塔尔是哪些特别的想法让他觉得自己是只老虎,而不是一只猫或别的什么动物。
马塔尔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说:“我觉得你正在啃我的腿,就像吃肯德基的鸡腿一样。我觉得你像头狮子,在你攻击我之前我要先出击。”
我一下紧张起来。看来事情并没有好转,马塔尔显然旧病复发了。他突然深吸了一口气,把头埋到膝盖里,从嘴里发出一声深沉得让人难以置信的咆哮声。
我的笔旋在空中,开始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捕食者和猎物会怎么做。哈姆迪坐在我的左边,门在我的右边。但我不想轻举妄动,我不想吓到他。马塔尔放在腿上的双拳紧握,而手指开始慢慢弯曲,好像有爪子长出来一样。他是在对我咆哮,而哈姆迪想说话时,他又向他咆哮起来。
“你要袭击我们吗?”哈姆迪问道。
“对,你们仨。”马塔尔说。
两位医生对视了一下,立刻开始用英语和阿拉伯语对他说话。
“放松点,马塔尔,没关系。你知道我们是谁,为什么咱们在这里。你想和海伦谈谈你的病情,还记得吗?”
马塔尔点点头。他似乎尝试和自己的冲动做斗争。他深吸几口气,突然又清醒了过来。他说自己需要抽支烟。拉菲亚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带着马塔尔走出房间。随着马塔尔的离去,我转向哈姆迪问他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在坚持服用他的药。”哈姆迪答道。他说,为了稳定他的病情,马塔尔本来一直在服用几种抗精神病、抗抑郁和抗焦虑的混合药物。“也许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最近没有服药。我想我们在这个房间里不是很安全。”
我表示同意并建议采访到此为止。但哈姆迪并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只需要换到一个更大的房间。
“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坐在门边,这样万一出了什么事你可以先跑出去。”
我绝对不想让马塔尔的病情因为采访而恶化,但我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因为这对于哈姆迪和拉菲亚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更好地了解马塔尔的病情和病因。于是我们换到一个大的会议室里,摆了几排椅子。
在我们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问哈姆迪为什么马塔尔的精神分裂会以这种变成老虎的罕见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他身上,而非其他病人呢?
哈姆迪说这可是个价值连城的问题。他说:“一定是有什么不一般的原因。这些变狼狂的患者认为自己的身体不是人形,而是各种动物。我们都对此非常惊讶。”
也许我们无法通过研究变狼狂的患者来直接找出答案,毕竟这些患者的人数太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就算没有得这个病,你也可能感到自己正在变身或出现了某些变化。其实有各种奇怪的病,有的让人不喜欢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有的是截肢之后出现了幻肢,还有的觉得自己变小或者变大了。也许其中的一些病例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塔尔的症状。要想了解这些,我们要先回到1934年的外科手术台上,一名剃光头的年轻男子正躺在那里,他神志清醒,但大脑却被打开了。
怀尔德·潘菲尔德将一根极其细小的电极插入年轻人的大脑表面。他按了一个按钮,使一股微小的电流穿过金属电极,下面的大脑表层微微颤动了几下。
“你有什么感觉吗?”他问病人。
“我的下巴有点刺痛感。”他说。
潘菲尔德的助手把结果记录下来,然后标记了刚刚被刺激过的脑区。潘菲尔德把电极移动了1厘米再次重复了实验,这次患者感到大臂被触摸了一下。
我们在第1章提到过潘菲尔德,那时他通过刺激海马体附近的脑区触发了病人的回忆。而这次他在鉴定患者的哪些脑区会引发癫痫需要切除,哪些组织是健康的他应该避免。当他做这种手术时,通常会先找出中央沟,这是一个位于大脑顶部的明显凹陷结构,它将额叶与顶叶分开。在这个标示性结构的前面就是条状初级运动皮层,这里某些神经细胞会向下伸展到脊髓,与直接控制肌肉的运动神经细胞相连。而中央沟的后面就是顶叶,其中包含一个相似的条带结构,被称为初级体感皮层,那里的细胞会接收来自身体各处的触感信息。当潘菲尔德刺激到初级运动皮层时,他的患者就会感到特定的肌肉在动。当体感皮层被刺激时,患者会产生被触摸的感觉。[9]
经过数百次类似的操作,潘菲尔德绘制出了一份触觉与肢体运动的脑神经图谱。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躯体以相应的顺序映射于大脑中,也就是说,在现实中相邻的躯体部位在大脑中也是相邻的。因此,大脑感受皮层中引起大腿触感和引起小腿触感的区域相邻,而这些区域又与负责脚踝、脚底、脚趾的区域相邻。
潘菲尔德描绘的这些身体图谱又被称为“小侏儒”——这是一个怪异的深蹲着的小侏儒,有着巨大的手掌、手指、嘴唇和舌头。这个畸形的侏儒代表了大脑中分配给不同躯体部位的区域大小与实际的躯体大小并不一致,而是与控制那里的神经末梢的发达度成正比。比如,“感官侏儒”之所以有着不成比例的巨大嘴唇和手掌,是因为嘴唇和手掌的触觉非常敏感,在大脑中占有很大的空间。感官侏儒的躯干和上臂等区域很小,是因为那里的神经末梢较少,因此占用的空间也很小。
这些大脑图谱对我们非常重要,它能让我们了解身体各处的感受,并且随时随地掌握自己躯体的位置。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怪——也许你以为自己知道躯体的感受是因为可以看到它——但事实上视觉信息并不是感知躯体的唯一方式。
闭上眼睛把手伸出来,试着触摸自己的鼻子。尽管无法看到自己的身体,你仍然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你的身体表征模型已经植入在大脑里了,科学家有时把这称为自体体感。要生成这个表征模型,不仅需要潘菲尔德的运动和感官图谱,还需要处理关节动作的本体感受图谱。而这些图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时刻都在更新,让你能自然顺畅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在哪儿,有什么感觉,在做什么。比如当你体重增加时,你看到的凸起的肚子以及来自皮肤和肌肉的感受会让大脑更新你的身体表征模型。尽管一些证据表明上顶叶参与了身体表征模型的建立(有的中风患者这个区域受损时不能识别自己的肢体),目前我们还没有搞清大脑中确切的产生位置。我们知道的是,这些身体图谱的相互交流最终产生了与实体匹配的自体感觉。而当这个系统出错时,我们就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
比如说幻肢。美国神经学家塞拉斯·威尔·米切尔(Silas Weir Mitchell)于1871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幻肢现象是指一些截肢患者仍然能感到失去肢体的存在,有时甚至感到疼痛的情形。在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战役期间,尼尔森勋爵失去了右臂。后来他将失去肢体之后的疼痛感认为是“灵魂存在的证据”。他说,如果一只手臂可以在实体被破坏后存活下来,那为什么整个人不行呢?
我们现在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灵魂存在的证据,但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神经的可塑性,或者说是我们一生中大脑可以不断变化的能力。当有人被截肢之后,曾经接受失去肢体信号的脑区就被闲置了。而大脑不喜欢浪费宝贵的资源,所以当一个肢体被移除之后,身体其他部位的映象会迅速侵占那个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幻肢,之前负责处理手臂触感的脑区现在可能被处理面部信息的神经细胞接管了。这样就会觉得截肢手臂被碰触,而实际上被触摸的是面部。
这些幻肢往往会产生疼痛感,比如幻肢手臂可能会感到麻木或者被卡在握紧的拳头里动弹不得。这可能是因为运动脑区还在试图向缺失的肢体发送命令而没有得到任何反馈。这些混乱的信息让大脑感到幻肢可能是瘫痪了。而一个简单的技巧几乎立刻就能缓解这种疼痛:把一面镜子放在患者的幻肢和完整的肢体之间,这样从镜子里看起来就像是有个和幻肢一模一样的复制品。松开拳头或者动一动完整的肢体就能让人产生幻肢正在做同样动作的印象。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缓解疼痛甚至使幻肢完全消失。
而我们不需要真的失去肢体就能体会一下有个幻肢在身体表征模型中是什么感觉。你只需要一个充气的橡胶手和两个小刷子,先把这个橡胶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用一块木板或纸板把自己的手遮住。然后请一个朋友反复用刷子刷橡皮手,同时用另一把刷子刷你的真手。一旦成功,你就会感到橡皮手真的就属于自己,而且能直接感受到毛刷的触感。
这只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其他实验表明我们身体的表征模型可以被轻易地改变。2011年,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和他的同事报道了一种称为截肢癖的新病症,患者虽然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理性,却不能自已地想要切掉自己健康的肢体。拉马钱德兰的第一个患者是一位29岁的男子,据他回忆,自己从12岁就开始有想要截断右腿的强烈愿望。他说这条腿让他觉得“过度完整”,他就是不想留下它。他承认这种感觉不正常,但在距访问拉马钱德兰一个月之后,他往自己的小腿上倒了干冰,由此迫使外科医生为他截肢。
许多医生认为这是病人引起他人注意的一种方式,或是过早面对截肢者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创伤。但拉马钱德兰认为,这更像一种有待理解的大脑生物学机制。
“当我们要求这些患者在他们希望截肢的地方画一条线,然后让他们一个月后再画一次,这条线位于同一个地方,”他当时告诉我,“这种精确度很难被解释为某种强迫症行为。”
为了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他还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神经科学家保罗·麦克乔克(Paul McGeoch)一起对四个截肢癖患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他们在碰触患者的腿部时扫描了每个人的大脑。
结果非常出人意料:当碰触被试者的“正常”腿或截肢部分画线之上的部分时,他们的右脑上顶叶有明显的激活。而碰触他们想要截肢的部分时,这个部位的神经活性没有任何变化。保罗团队认为,右脑的上顶叶是大脑中综合不同类型感受输入的理想位置,从而创造出统一的自体体感。他们提出,在某些非常情况下,有人感觉到肢体被触摸而触觉不能融入他的身体表征模型,这时就产生了截肢癖,因为他们想要排除属于异己的部分。[10]
有趣的是,类似的原理可以解释为什么跨性别者经常对自己本身的性别感到不满。最近,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劳拉·凯斯(Laura Case)和她的同事招募了8名被试者,他们是具有女性的解剖学特征但又有强烈的意愿成为男性的跨性别者。作为对照,他们还招募了一组非跨性别的女性。为了比较他们大脑对性征器官的处理方式是否一致,凯斯和她的团队在碰触每个被试者的手或乳房时扫描了他们的大脑。果然,在对照组里碰触手或乳房都会导致顶叶的相应区域被激活。但是在跨性别组中,大脑对乳房触摸的反应要显著低于手的碰触。[11]
在这两项研究中,我们都遇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断定大脑中显示的差异是人们对特定身体部位产生厌恶的原因还是结果。尽管如此,这两个实验都明确地展示出我们大脑内部存在着一个身体表征图谱,而且大脑顶叶在这个图像生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些发现能够解释变狼狂症状的产生吗?
早期的一些观察表明是有可能的。1999年,哈姆迪遇到了一位53岁的病人,患有癫痫和严重的抑郁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不能自已地感到自己长出了爪子。脑部扫描显示她的顶叶一侧有组织受到了损伤。这个结果表明,当变狼狂患者感到自己在变身时,他们的大脑可能确实感受到了这些变化。
同时我们还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容易产生体感幻觉,比如前面提到的橡皮手的小把戏。脑部成像扫描表明,这可能是由于大脑中储存躯体表征的信号较弱,而对来自视觉和运动皮层的感官信息有更强烈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长出的爪子或动物的面部等视幻视能够轻易地融入我们的体感表征模型中。
可惜对马塔尔的脑部扫描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异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正常,和我讨论过这种病情的几位医生一致认为,未来更好的神经成像技术和更高的分辨率将有助于揭示出变狼狂和其他精神分裂症的成因。
“现在有多种假说和一些解决方案,但如果想得出任何可信的结论,我们还需要对更多患者进行扫描,并做更大规模的研究。”哈姆迪说,“而在现阶段,我们会继续治疗马塔尔的精神分裂症,并希望这能缓解他的变狼狂症状。”
回到艾因的医院中,拉菲亚带着马塔尔和3位年轻医生进到我们所在的会议室。在马塔尔抽烟的时候,拉菲亚了解到他的母亲带着他的妹妹去了印度。因为他的妹妹也开始出现精神分裂症的迹象,所以她去了一家专门的诊所进行检查。拉菲亚也认为马塔尔没有在服用药物,再加上母亲的离去引起的焦虑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症状。
马塔尔走进会议室的时候精神状态看起来有所好转。他在前排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我们继续吧。”他看着我说道。
我朝他微笑致意,又让他讲讲当有这种变身的感受时是怎么知道自己是老虎而非其他动物。
这次他立即流利地做出回答。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知道的,我只知道我就是老虎。我还听到自己周围有很多声音,说我糟透了。他们嘲笑我,还说我是垃圾,我不配做人。有一阵我觉得周围有一头狮子,有时它会攻击我,从后面抓住我的脖子。我没法逃离这种痛苦,我能看到自己被攻击的地方流出许多鲜血。”
“你觉得自己有办法保护自己吗?”
“完全没有,”他摇了摇头,“我无法让自己免受狮子的攻击。它比我强大得多,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先出手。”
“每次这种感觉会持续多久?”
“有时只有几分钟,有时长达几个小时。”
哈姆迪突然打断他问道:“你最近有这种感觉吗?还是只有今天早上才出现?”
“从昨晚就开始了,”马塔尔说,他看起来有些急躁,“我当时在床上突然就有这种感觉,于是我锁上门把毛巾盖在头上用床单把自己裹起来,这样我就不能动弹或者乱跑了。”
他说曾经有一次,当他还是无法抑制他的冲动时,他就会在鞋子上贴上水泥块,让自己的脚非常沉重而无法四处移动。
“我只想尽量阻止自己伤害到其他人。”
“当你感觉变成老虎的时候,有没有照过镜子?”我问道。
“有的,”他说,“当我感到自己变成老虎时,我照镜子会看到两样东西:自己是一只老虎,还有一只狮子抓住了我的头和脖子。我完全不能理解看到的一切,只觉得非常可怕。”
虽然他今天的表现不正常,但医生们并不认为马塔尔会对他人构成危险。他的药物也一直使他能够进行正常的社会活动,并安全地生活在当地社区。
“我们愿意让他住在家里,他在那儿能得到家人和社区护士的照顾,”哈姆迪说,“和英国的文化不同,这里的人们非常重视家庭对病人的看护。”
我又转向马塔尔:“除了服用那些药物之外,你还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自己的妄想发生吗?”
“我总是穿白色衣服,”他说着,指了指自己的白色全袖长袍和头巾,“这让我感到平静。在我看来白色是一种和平的颜色,它能缓解我那种奇怪的感觉。”
但刹那间气氛又变了,马塔尔突然发出大笑。他伸出手弯起手指关节,并低下了头甩掉了鞋子。接着他抓住自己的左腿,并露出痛苦的表情。
突然,咆哮又开始了。
“我觉得咱们得走了。”坐在我旁边的医生说。另一位医生问马塔尔要不要吃些药来缓解一下他的焦虑,他点点头,瞥了一眼房间就离开了。
我很希望自己可以在结尾补充说,马塔尔现在痊愈了,药物鸡尾酒疗法和心理治疗帮助他彻底消除了那些妄想。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回家几个月后,我给拉菲亚发了封电子邮件,请她把我的便条翻译给马塔尔并感谢他接受采访。我也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拉菲亚很快回了信,她说马塔尔在采访当天的行为显示出比较严重的复发,后来他的病情多次反复并入院治疗。她说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功能水平。
也许马塔尔的大脑非常独特,但我们可以从这个极端的案例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家庭成员的强大亲情和悉心照料,使得这些病人病情能够稳定下来,而不需要长期住在看护所。正是从这些变狼狂患者和其他躯体体感症患者身上,我们了解到自己的大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让我们能时刻产生这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感觉: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体。
大家都在看
-
1994年,人类第一次亲眼目睹星际天体撞击事件,有多可怕? 1994年7月间,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和木星亲密接触,而我们人类距离木星3092万公里远的地球表面,目睹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行星撞击事件。在此之前,我们只是在书本、影视作品和想象中见识过各种行星之间互相撞击的场景, ... 人类之最11-24
-
为什么我们察觉不到人类在进化?难道人类已经停止进化了吗? 对于进化论的探讨往往充满争议,很多人不愿将自身祖先与猿猴挂钩,更不用说承认与黑猩猩有血缘关系,尤其是起源于偏远的东非之地。但事实上,达尔文在提出《物种起源》时,进化论还远远不是科学的范畴,它更像是博物 ... 人类之最11-17
-
地壳中含量最高的十大元素,氧、硅和铝分列前三名 在地质学术语中,地壳是岩石的固体地壳,是地球固体球的最外层,是岩石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球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的,其中最多的有氧、硅、铝、铁、钙等。截止目前,已经发现的118种元素中,其中94种存在于地壳中;那 ... 人类之最11-16
-
自我是人类最私密的所有物,却非常依赖人类的社会性 齐格蒙特·鲍曼是近几年在国内广受关注的一位社会学家、思想家。他的作品《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将熟悉变为陌生》等都掀起了阅读热潮。今年,有关他与塔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瑞恩·罗德的对谈录《自我》上市。在 ... 人类之最11-15
-
揭开人类制度变迁的秘密《人类命运:制度治理》西安发布会举行 2024年11月10日,《人类命运:制度治理》新书发布会西安专场举行。王晶作为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曾白手起家参与创办两家高科技上市公司的企业家、高级工程师和享受国 ... 人类之最11-14
-
人体最脏的部位,很多人都用舌头舔过,今天总算知道,长记性! 声明:本文内容均是根据权威医学资料结合个人观点撰写的原创内容,在今日头条全网首发72小时,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为了方便大家阅读理解,部分故事情节存在虚构成分,意在科普健康知识,如有身体不适请线下就 ... 人类之最11-14
-
人类现在有没有可能是宇宙中最高等的文明? 在那浩瀚无垠的宇宙深处,是否存在着其他智慧生命?而人类,现在有没有可能是宇宙中最高等的文明呢?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思考宇宙的广袤程度。宇宙之辽阔简直超乎想象,包含着数以亿计的星系,每个星系又拥有 ... 人类之最11-11
-
湿气是癌症的元凶,按摩人体这个“阳气窝”,逼出骨缝里的湿气 《黄帝内经》中提到,肿瘤的病因是“邪气居其间”“久而内着”。脾虚生痰,肺、脾、肾功能失调,水湿代谢紊乱,则停聚而成痰,随气流行,外而经络筋骨,内而五脏六腑,全身上下内外无处不至,结为痰核,而成肿块。临 ... 人类之最11-10
-
「最」系列!你知道人体的世界之最吗? 世界上最长的"管道"人体身体一共有一千多亿条纤细的微小血管,没错掰掰手指数一下,1000多“亿”条,如果把这些微小的血管全部连接起来,几乎长达10万公里,可绕地球两周半。 世界上的最奇特的"钢筋" ... 人类之最11-08
-
这本百万年史书,藏着多少秘密 这本百万年史书,藏着多少秘密半月谈记者 杜一方桑干河畔,泥河湾沟壑纵横间,埋藏着文明起源跨越200多万年的秘密,被誉为“东方人类摇篮”。这里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已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人类起源时间推前至约 ... 人类之最11-07
相关文章
- 人体最脏的部位,很多人都用舌头舔过,今天总算知道,长记性!
- 世界最极端的十个人类居住地,温度常年零下70度,竟有人在此定居
- 人体免疫力最喜欢的6种主食,隔三差五吃一次,提高免疫力少生病
- 人类现在有没有可能是宇宙中最高等的文明?
- 湿气是癌症的元凶,按摩人体这个“阳气窝”,逼出骨缝里的湿气
- 「最」系列!你知道人体的世界之最吗?
- 这本百万年史书,藏着多少秘密
- 世界千米级高楼:竟出自这位80岁建筑师之手
- 人类最悲壮的一次阅兵:走过主席台直扑战场,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 从权利的分封性质看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进步历程
- 希腊神话里的五代人类,他们都有啥奇特之处?又是如何灭亡的?
- 人体这5个地方最易“藏”血栓!不想被“栓”住,这5个动作要少做
- 《永乐大典》,消失殆尽的中华瑰宝,人类历史最恢宏的百科全书。
- 面试难题:人体最不怕热的器官之思》 在河南
- 王嫩人体油画:裸而不俗,美而不媚的艺术珍品
- 四个已被科学家证明,可人类却难以接受的理论,看看有哪些?
- 太震撼了!人类造出十大逆天之物,堪称世界最难,颠覆你的想象!
- 人类交配会产生快感,但分娩时很痛苦,真是自然进化的最优解吗
- 人体免疫力最喜欢的十种主食
- 人类医学史上最伟大的 20个发明,你知道多少? 1
热门阅读
-
关于男人的15个世界之最,最长阴茎达56厘米 07-13
-
东方女性最标准的乳头(图片),看看自己达标吗 07-13
-
人体器官分布图介绍 五脏六腑的位置都在哪 07-13
-
木马刑是对出轨女性的惩罚 曾是满清十大酷刑之一 07-13
-
熙陵幸小周后图掩盖性暴力 至今保存于台湾博物馆 07-13
-
包头空难堪称国内最惨案件 五名遇难空姐照曝光 07-13
-
2022中国最新百家姓排名,你的姓氏排第几? 03-26
-
好玩的绅士手游有哪些?2022十大绅士游戏排行榜 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