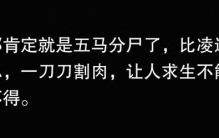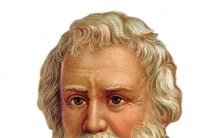银河之于人类,还有多少浪漫与治愈?
作者:曹菲璐
童话《银河铁道之夜》是日本作家宫泽贤治(1896—1933)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作品讲述少年乔凡尼因父亲失踪而被同学排挤,同时还要照顾病弱的母亲。疲惫的他在梦境中与朋友康帕瑞拉登上开往天堂的银河列车,最终感悟到幸福真谛的故事。作品最初写于1924年,作者三易其稿,直到离世仍未修改满意。但宫泽贤治自己倒也曾说过,“永远的未完成才是所谓的完成。”这部未完之作留下了极具开放性、可能性的改编空间,其瑰丽浩瀚的银河意象,给予众多俯仰宇宙、穿梭星河以求心灵治愈的艺术家以启迪,包括成为漫画大师宫崎骏重要的灵感来源。
《银河铁道之夜》1985年就曾改编成动漫电影,也有音乐剧版搬上舞台。音乐剧以原作“消失的父亲”为引,串联孤独症患者乔凡尼与朋友遨游银河的自我治愈之夜。
而在《银河铁道之夜》初稿诞生百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第十七届文学节上演的话剧版改编,则一反先行者们对这一故事的演绎,以逆行的姿态试图进入宫泽贤治童话文本深处——无视人类的集体痛苦,便没有抽象的幸福可言;叩问动荡不停、结构性困境加剧的世界,反思已无法从梦境和想象中汲取力量的现代人的处境,凝视旷远银河的意义。
拒绝造梦
提到宫泽贤治,绕不开的便是他并不得志的创作生涯。尽管生活的苦痛的确造就了他作品精神避难所般纯净澄澈的意境,但梵高式的艺术传奇还不足以让我们全面理解他作品中那一抹化不开的哀伤。与他的文学创作同步展开的,还有他与农民紧密联系的奋斗岁月。
1896年宫泽贤治出生于日本极度贫困的岩手县的一个经商家庭。优渥家境与贫困同乡的巨大差异,让年幼的宫泽贤治省思,也为他20多岁时与家族产业决裂埋下了伏笔——1915年,因不满家中生意建立在对农民的压榨之上,年轻的宫泽贤治选择走向农民,考入农林学校,后来受聘为郡立养蚕讲座所的教师,与父亲决裂后孤身在东京过着清苦的生活。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以一场空前的天灾加剧了日本的危机感。1926年昭和时代开启,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彻底脱缰,“新大陆政策”也在这一时期问世。宫泽贤治辞去教职,回到因政客穷兵黩武而境况雪上加霜的故乡,带着深重的愧疚感与赎罪感开始改造故乡。他白天与农民共同劳作,为解决稻热病和旱灾四处奔走,改良石灰制法,背着40公斤的碳酸石灰去东京售卖和宣传;夜晚向农民传授农学技术,普及文化知识。他还用戏剧、童话、音乐等艺术形式,实现自己改造农村、为民造福的信仰和理想。这种透支自我的苦行生活,让宫泽贤治最终积劳成疾。他在论文《农民艺术概论》的序言中写道:“在全世界变得幸福之前,没有个人幸福可言。”
话剧版《银河铁道之夜》把握住了这条关于幸福观的脉络和内核。演员们对着观众猝不及防地齐声念诵“无法离开”,使得这辆银河列车的旅程充满了诡异感,有意质疑以往重生梦境、银河列车、星际遨游提供的那种天然意味着治愈、幸福、救赎的叙事。
《银河铁道之夜》的主创团队拒绝造梦,用歌队的介入来打破整一的叙事;同时营造了一个荒诞游戏的外壳,以尺寸合适的插科打诨将观众从廉价的剧场诗意中抽离;将战争、经济、性别议题等召唤进剧场,映射出当下被撕裂的世界图景。
《银河铁道之夜》原作的底色是悲伤的,话剧版也如此。从第四场开始,该剧的内容逐渐与其游戏性的外壳相游离:加入“亚麻头发的少女”这一角色来承担女性主义的探讨,通过雅赞、米娜兄妹为代表的遇难儿童反思当今战争,让捕鱼人拉米雷斯身上映出政治投机分子的影子。通过这些“布莱希特”式的手法,揭示出一个非常宫泽贤治的观点:如果不对当前的存在进行反思,我们便被包裹在这样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个人幸福可言。
不必重生
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宫泽贤治为何在通往天国的列车上安置葬身海难姐弟的角色,又为何令乔凡尼等乘客看到奔跑在原野上的欢乐的印第安人,及其背后的讽刺性。1933年宫泽贤治去世时,20世纪人类最残酷的浩劫才刚刚拉开序幕,他似乎仍然相信笔下的银河之旅能对改变现实世界发挥作用,“从梦境中醒来”作为一种重生的符号,仍能被赋予某种“希望”的意义。
但话剧版《银河铁道之夜》无疑提炼并深化了原著中的反战意识,将这一对因无妄之灾而丧生的姐弟,转换为在战争冲突中丧生的少年。他们来到列车上是为了“寻找长大的方法”——相信观众能够辨识出这句话对应的是“我在巴勒斯坦长不大”。剧中哥哥雅赞以“配音+玩偶”的形式出现,为观众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让人怀疑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还是妹妹米娜的幻想,唤起观众对战争给孩子带来精神创伤的思考。
另一个具有想象力的改动是“捕鱼人”形象的变化。这一形象来自原作中的“捕鸟人”——一位捕捉银河中糖果质地的大雁和白鹭的诡异老人,宫泽贤治为他留下了许多疑点没有解答。到了话剧中,捕鱼人拉米雷斯的形象,则被赋予了拉美爆炸文学作家波拉尼奥笔下的1960年代拉美知识分子的形象——曾试图跻身左翼,又因政变失败转向右翼,用酗酒、写诗、嗑药麻痹对动荡生活的实感。编剧将拉米雷斯流放于时间之外永受凌迟。这一对他的审判和惩罚,源于拉米雷斯自己对“被铭记”的执念:将革命信仰作为吸引政客眼球的谈资和筹码,在左右之间灵活地切换,以达成他的英雄想象。
话剧版《银河铁道之夜》试图推翻的是不加思辨的“幸福”,是在梦境中得到所谓的启迪并可以遗忘现实痛苦的“重生”。因为你一旦意识到话语霸权、消费主义对人的侵蚀和控制,一旦听到世界动荡之下远方的哭声,一旦痛苦而清醒地生活过,便无法再神经粗粝地度过一生。
不再神秘
《三体》中曾经写道:“光的传播沿时间轴呈锥状,物理学家们称为光锥,光锥之外的人不可能了解光锥内部发生的事件。想想现在,谁知道宇宙中有多少重大事件的信息正在以光速向我们飞来,有些可能已经飞了上亿年,但我们仍在这些事件的光锥之外。光锥之内就是命运。”
当人们只能被动承受信息的光锥穿透自己,是该宿命论地存在还是积极地做出选择?话剧版《银河铁道之夜》给出了一种答案:它未必是像浮士德一样在重生之后追逐爱情与事业,而是一种“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体验观。笔者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设定是,这趟银河铁道列车并未言明一定通向天堂:它以一个有些诡异的循环模式使乘客乔凡尼成为下一个领航员,与新的乘客相遇,再度开启一个“无法离开”的旅程。
颇为巧合的是,就在话剧版《银河铁道之夜》上演前后,网络上正在热议“月球20亿年前就已死亡”这一话题。千百年来曾经寄托无数浪漫思念与哀愁的月亮,突然被解构成与地球如影随形的死尸。随着更多天体物理学的概念和成果被转化成科幻小说、影视作品或当代热梗,遨游宇宙也更多地与人类自身文明的危机相勾连:银河、星体、物质还是否浪漫?凉风和酒是否还能勾连相同的怅惘?
当然,这部由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共同打造的作品也留下了遗憾。比如演员身体训练的欠缺使得表演的严肃性不够,难以通过姿态达成反讽的目的;还有配乐等方面暴露的专业性不足。此外剧作还有更重要的部分有待完善:来到这辆列车上的人们到底有着怎样的共性?他们为什么会遇到亚麻头发的少女、战争遇难的兄妹和捕鱼人拉米雷斯?主人公乔凡尼的车票因何特殊于所有乘客?这些问题的呼应有助于使松散的表现式剧情更加自洽,让一部带着先锋气质的作品完成它真正想要的表达。(曹菲璐)
大家都在看
-
“彩云之南”隐藏着什么世界之最,为何荒蛮边地竟成文明熔炉? 在中国西南边陲,有一片被北回归线横穿的土地,这里山高谷深、民族纷繁,曾被中原王朝视为“瘴疠之地”。然而,这座看似蛮荒的高原,却藏着改写人类历史的密码——5.3亿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此定格,两千年前的 ... 人类之最04-14
-
论人类最可贵的四大品质 在战争与和平交织的年代里,人类总能诞生出一些品质如同星辰一般,指引着我们突破走向光明。人类最可贵的品质有四种!最后一种更是出人意料!一、仁爱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 人类之最04-14
-
你知道人类史上最残酷刑罚是什么吗?凌迟在它面前只是个弟弟 友友们大家来啦!今天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精彩话题老规矩先点赞再看文!那年夏天,村里头的老李头儿,他那俩儿子,一个得了绝症,一个因为工地出了事。老李头儿家穷得叮当响,我那会儿刚毕业,没地儿找工作,就想着帮帮 ... 人类之最04-08
-
绝境中的微光: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希望密码 敦煌莫高窟第254窟的壁画上,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穿越千年依然震撼。当王子坠入悬崖的刹那,画家特意在云层中勾勒出若隐若现的佛光——这是绝境中最古老的希望图腾。在切尔诺贝利核废墟中,生物学家发现一种特殊 ... 人类之最03-29
-
人类全身上下最强韧有力的肌肉,竟是舌头? “舌为心之苗”,在中医理论中,舌头被视为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窗口。而在现代科学的视角下,舌头同样有着诸多令人惊叹的特性。关于“人类全身最强韧有力的肌肉是舌头”这一说法,虽然存在一定的误解,但舌头的独特之 ... 人类之最03-28
-
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十大发明!第七个让全球沸腾,你每天离不开它! 从钻木取火到人工智能,人类用智慧点亮了文明的曙光。这些看似普通的发明,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重塑了世界格局!今天,就让我们盘点史上最伟大的十大发明,看看哪些发明让你惊叹不已?1. 车轮(约公元 ... 人类之最03-24
-
人体最强大的能量,都是来自于心神合一、内守灵魂本源 在现代的社会中,我们常见许多人被情绪左右,从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能量。试想,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繁琐的事情或者在生活中面对困境,是不是常常觉得难以集中注意力,甚至陷入无休止的烦恼?而这种情况,大多数时候 ... 人类之最03-24
-
一起来认识一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科学家 人类文明的灯塔:十位科学先驱的永恒光芒在人类文明的漫漫长河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着认知世界的征程。这些科学先驱以智慧为火炬,以探索为舟楫,在时空的维度上镌刻下永恒的精神丰碑。从古希腊的思 ... 人类之最03-21
-
合集•人生感悟之三:人类最珍贵的是真心实意 人真心实意的互相关爱、互相帮助,则人与人之间美好、家庭与家庭之间美好、国家与国家之间美好、人类世界之美好。△共同创建和谐、幸福美好的社会什么是真心实意所谓真心实意(是个成语):指的是心意真实、真诚,毫 ... 人类之最03-14
-
人类极限大赏:生活中那些惊掉下巴的“世界之最”! “你总觉得生活平淡无奇?那是因为你没见过这些‘疯狂’的人类!”当普通人还在为早起打卡、减肥健身发愁时,地球上却有一群人用行动诠释着“极限”二字。有人用62年不剪指甲换来一副“九阴白骨爪”,有人为一口美食 ... 人类之最03-03
相关文章
- 一起来认识一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科学家
- 合集•人生感悟之三:人类最珍贵的是真心实意
- 盘点张家口的全国以及世界之最
- 人类极限大赏:生活中那些惊掉下巴的“世界之最”!
- 中国最伟大的人—毛泽东
- 人类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三大死亡事件,最后一个让人脊背发凉!
- 陕西深山现身5万年前人类头骨,竟暗藏华夏先祖进化的印记?
-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四大哲学家,他们分别是哪四位?
- 世界十大核事故排名:苏联排行第一,日本美国各占一半
- 世界十大食人魔:张永明上榜,第四名凭借吃人在日本混的风生水起
- 史上最漂亮的十大化学实验:人工染料上榜,第十获得诺贝尔奖
- 世界上最好学的五大语言,西班牙语排第一位
- 人类极限的最强数值#世界之最
- 当AI凝视人类:那些算法无法解答的终极之问
- 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四种酷刑,让人毛骨
- 为什么说乾隆是整个人类史上最舒服的帝王?
- 兔子造成人类史上最严重的生物入侵?澳大利亚任命“野兔总管”
- 韩江:去凝视人类最柔软的部分
- 上帝手抖合集,那些人体器官之最!
- 我国首部太空实景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创下人类多个“之最”
热门阅读
-
关于男人的15个世界之最,最长阴茎达56厘米 07-13
-
东方女性最标准的乳头(图片),看看自己达标吗 07-13
-
人体器官分布图介绍 五脏六腑的位置都在哪 07-13
-
木马刑是对出轨女性的惩罚 曾是满清十大酷刑之一 07-13
-
熙陵幸小周后图掩盖性暴力 至今保存于台湾博物馆 07-13
-
包头空难堪称国内最惨案件 五名遇难空姐照曝光 07-13
-
2022中国最新百家姓排名,你的姓氏排第几? 03-26
-
好玩的绅士手游有哪些?2022十大绅士游戏排行榜 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