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编者按:著名音乐家坂本龙一于3月28日病逝。《音乐即自由》一书是坂本龙一于2009年出版的口述自传,书中记录了他在乐队YMO时期的狂傲自信,也有为电影《末代皇帝》配乐时的惊心动魄——在两周内疯狂作曲44首,并带着斐然的成果登上奥斯卡的舞台。
下面这篇书摘讲述了坂本龙一在现实关怀下进行创作的历程。提到的专辑《裂缝》(Chasm)以9·11事件后美国入侵伊拉克为契机,融合了东洋旋律和嘻哈等元素,听感多元而略显割裂,这也反映出坂本龙一对世界本身充满断裂的悲观感受。2008年的格陵兰岛之旅加深了他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由此创作出了崭新的音乐。坂本龙一经常率真地自嘲“消极又被动”,但面对人类苦难时却觉得“必须做点什么”。
本书戛然而止于2009年,以名为“终曲”的后记作为结尾,现实中,健康情况长期堪忧的坂本龙一还是迎来了自己的终曲。他擅长从古典音乐中汲取养分,并以实验性的姿态挑战流行音乐范式,他的音乐也因此广博、大气而难以定义,它们甚至不总是悦耳的,但似乎也正是这些“不悦耳”,更加印证了坂本龙一以音乐介入现实的力度和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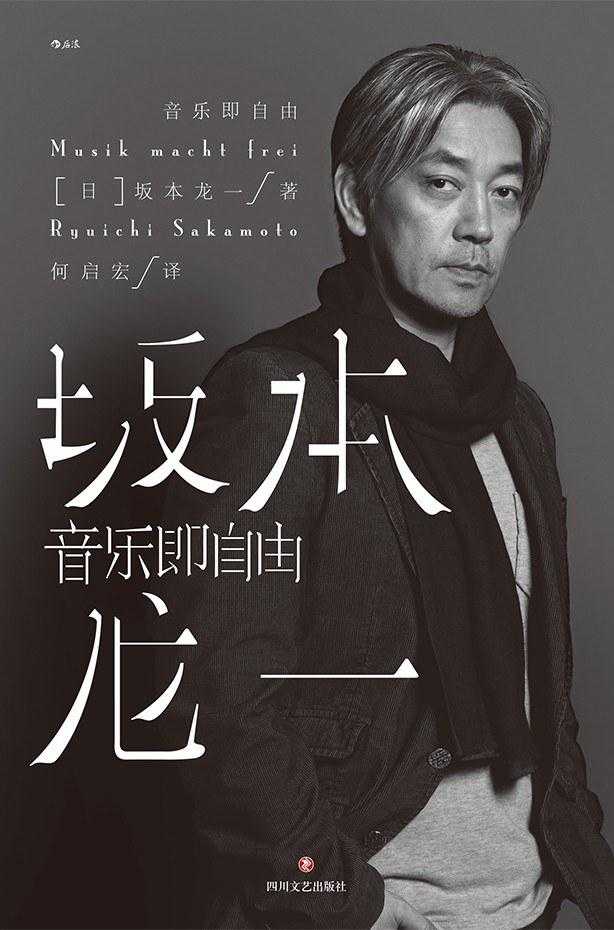
《音乐即自由》(节选)
作者 | [日] 坂本龙一
9.11事件后的殖民反思
(9.11事件后)音乐工作也不能因此一直停摆,所以不久后重新开始。恐怖袭击事件后,我接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纪录片《奇迹泉》的配乐。
整部片子的舞台位于白俄罗斯的一个小村庄。由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变,这里遭受了辐射污染。虽然辐射污染的程度极为严重,但是村里的老人却不愿撤离。村里有一口全村共享的涌泉,结果在调查时,发现泉水丝毫没有遭受污染。于是,这口涌泉就成了村民心中崇敬的神圣之泉。虽然只是一口微不足道的涌泉,对村民来说,却是最实际的救赎。
我当时一直担心恐怖分子会用核武器发动第二波攻击,因此电影中所描绘的核能污染的恐怖情景,对我而言十分贴近现实,于是在创作配乐时,我投入了相当多的情感。即使现在再听,眼前似乎仍会浮现自己当时恐惧的样子。
不久之后,我又接了两部电影的配乐工作。一部是布莱恩·德 ·帕尔玛执导的悬疑片《蛇蝎美人》,另一部是拍摄德里达生活的同名纪录片《德里达》。这段时期,我依旧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下,不过这些工作都有截止期限,所以不得不去完成。就在这样创作音乐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恐惧稍稍平缓下来。或许只是因为自己沉浸在工作中,所以无暇多想。这样的解释当然也不无可能。然而,我想原因不会如此单纯,应该是有音乐的某种力量在我身上发生作用吧。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我越来越觉得,让“9·11”恐怖袭击酝酿成形的整个大环境,全都是霸权国家美国一手造成的。但另一方面,无论是音乐还是文化,我至今所获得的信息都是经由美国传输而来的,不仅是摇滚音乐,甚至连东方思想、禅学文化都是。

总算还有属于欧陆产物的古典音乐,但若是少了欧洲的霸权主义、殖民地主义,这项产物也无法成形。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这样的产物是多么难能可贵,而如今对于这么想的自己,我则感到不以为然。无论是德彪西、马拉美、披头士,还是巴赫,一切的美好都是假象。即使是现在,我仍有这样的想法。然而,这些假象却是我唯一拥有的表现方式。即使德彪西的音乐可说是人类史上最精湛的作品,其中仍含有法国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的犯罪性。针对这点,我想还是要有所意识。
感受到“世界断裂”的音乐
2004年,我发行了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一张专辑Chasm。“Chasm”的意思大概就是裂痕、断层。用这个单词当成专辑名称,我觉得相当直接,又充满了理念。
制作这张专辑时,我深刻感受到存在于世界上的断层,或许可以特指当时美国与其他世界各国间的断层。这个时期也频频有人指出类似的矛盾隔阂,例如过去的美国与小布什政权下的美国、孤立主义的美国与较为多元化的世界、帝国主义的美国与走上街头反美的全球人士,还有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对立,等等。不过,我并不认同“文明的冲突”之类的论点。
“9·11”恐怖袭击发生的2001年,这类断层已经越来越清晰可见。2003年,美国开始进军攻击与这起事件应当毫无瓜葛的伊拉克,更是将这样的断层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当时不论怎么分析推敲,我都觉得美军进攻伊拉克的动机并不单纯,现在也还是认为事有蹊跷,但是都没有人直言出来。虽然一般大众走上了全球各地的街头,发出这样的疑问,但是从事思想、言论或新闻报道等相关工作的人,却是一声不吭。对于这种情形,我完全看不下去,每天痛心地想着,这是在开什么玩笑。在这样的过程中制作而成的专辑就是Chasm。我当时就是为愤怒所驱使,在不得不做的心情下,制作了这张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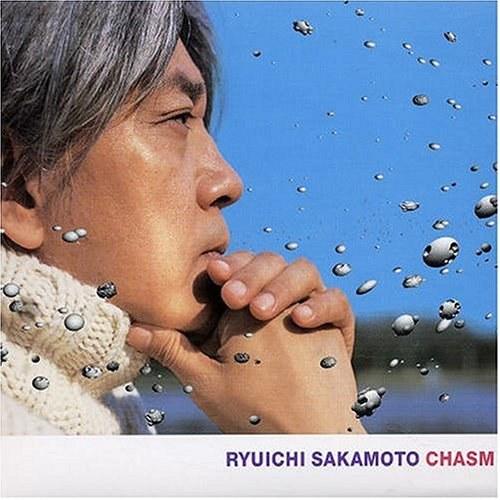
这段时间,我也开始与卡斯顿·尼古拉、克丽斯汀·凡尼希等人合作专辑,他们都是年纪小我一轮以上的年轻人,带给我非常正面的刺激。我成长过程中听过的现代音乐,好比施托克豪森、泽纳基斯等人的作品,在他们的音乐中全都融合为一股源流。而且,他们的音乐定位是通过CD形式流通的一种流行音乐,而不是专门写给少数乐迷的现代音乐。我很高兴彼此之间宛如有着共同的精神源头,而且我旧有的思考模式仿佛也因为他们而有了新的触发,不再认为创作流行音乐就得将前卫音乐的某些元素封印起来,于是,我的音乐道路似乎变得更为宽广了。
“被迫无奈”投身于社会运动
在我1999年创作的歌剧LIFE里,蕴藏了许多与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相关的信息,而且还请来宗教人士参与演出,因此也带着宗教色彩。大概是从那段时期开始,突然有许多团体来找我,例如倡导反核与和平的团体、处理霸凌与虐待事件的非营利组织,或是为原住民发声的群众组织等,真的是应有尽有。
曾经有一段时间,或许是因为宗教人士的影响,一般被称为新世纪派系的宗教团体也来找过我。他们游说人的说辞相当厉害,感觉好像是坂本总算也加入了我们的团体,不过根本就没有那回事。总而言之,许多工作的委托接踵而至,但是在我的不断拒绝下,这样的情况总算平息下来。
之后,我在“9·11”恐怖事件发生的那年出版了《反战》,或许由于这个缘故,许多工作委托再度从各地涌来,数不胜数。在美国,演员或运动选手等公众人物经常会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在先前的日本,不论立场是保守或改革,仍有一些身具风骨的达官显要敢于对社会直言,然而现今的情况却是全然不同。或许正因如此,这类相关问题就会找上像我这样的人。
然而,我几乎不会去主动号召,不让自己与这类社会活动有所牵连。对于这些事情,我一直都是谨慎看待,希望能免则免。话虽如此,一旦发生的问题与自己切身相关,身为当事人之一,有时无论如何也不得不参与。

至于后来的活动部分,我在2007年发起的森林再造保育计划“More Trees”(更多树木),现在正逐步确实地扩展开来。简单来说,“More Trees”就是一项增加森林的活动。森林有助于减缓地球变暖速度,并且确保土壤的保水力与生物多样性。为了让参与人士也实际感受到通过这项活动再造森林的喜悦,我们下了许多功夫。这是一项相当有趣的计划。
2007年11月,我们在高知县梼原町种下了第一片森林。2008年8月,在同为高知县的中土佐町完成了第二片森林的再造工程。不久之后,我们预定要在菲律宾种下第三片森林。这项活动发起至今,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森林逐步增加,完全超乎我的预期。第三片森林的面积也相当大,因此能够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大幅提升。日本终于要开始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因此这波森林再造保育的趋势应该会越来越热门。
我虽然投身这些活动,却也不曾想过要将关注的焦点扩及全球的状况,做出什么积极干涉的动作。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所以站在我的立场来说,都是迫于无奈才会去做。我要一直说服自己:“没办法,做都做了。”在我依然游移不定的时候,这项活动已经逐渐推广开来了。
格陵兰岛之旅
2008年秋天,我参加了“法韦尔角”(Cape Farewell)计划,去了一趟格陵兰。这项计划是与科学家和艺术家一同去观察气候变化的实际状况,并且将看到的结果传达给世人。直到出发的前一天,我还是觉得麻烦死了。然而,心不甘情不愿地参加了之后,感觉却如获至宝。眼前看到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甚至回到纽约后,还是很难回归到日常生活。
真要说起来,就连YMO,我也是受邀才加入的。也会觉得,为什么当初要答应这个邀请呢?不过,细野主动邀请,让我觉得很开心。仔细想想,自己积极开始的事情应该不多,真的是消极的人生。

就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不太会去扩展自己的世界,反而是尽可能地封闭自己,只要能够创作音乐,就感到相当幸福了。不过,环境却让我和许多事情有所交集,而且也获得许多体验,真的是命中注定。
我有许多次针对环境问题发言的机会,或许因为如此,我经常被问到:“环保音乐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基本上,我认为根本没有这种音乐。不过,我也一直在寻找答案,如果真有所谓的环保音乐,虽然不是什么“人之死”之类的概念音乐,不过大概也会是某种否定人类一切的音乐吧。一神教的主义,也就是有起始必有终结的论点,或是历史有目的之类的观点——像这种人类思考出来的概念,我希望尽可能地不去碰触。 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而且也呈现在这次发行的专辑里。
我觉得去过格陵兰之后,自己音乐中呈现的感觉大概有了极大的变化,作品的方向性也变得更加鲜明了。自己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启发?我一直努力地想要反刍整理这次体验的意义,但至今仍无法顺利地用言语形容,或许也只能说是为大自然的雄伟所慑服。数量惊人的海水与冰山,由海水与冰山造成的风景与寒冷气候,对于这些景色的印象太过强烈,让我彻底无言。

有一句话是说,人类要守护大自然。论述环境问题时,经常会引用这句话。然而,我认为这几乎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人类加诸大自然的负担超出大自然容许的范围,受害的当然会是人类。伤脑筋的会是人类而已,大自然不会感到任何困扰。看到大自然的雄伟、强大,会觉得人类实在不值一提。生活在那片冰山与海水的世界时,我不断感到人类是多么微不足道,我甚至也觉得人类或许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即使回到纽约,我觉得自己的灵魂似乎还留在北极圈,因此没办法回归到文明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直到现在,我似乎还是一直想要回到那里。美国的新总统选出来了、金融危机造成的可称为恐慌的状态正逐渐蔓延,然而就算出现如此重大的事件,我还是觉得实在没什么大不了。
我现在身在纽约的曼哈顿,这里可说是全球最富人工色彩的地方,金融危机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我在这个地方创作的音乐,说不定最后会与人类世界,或是现在的事件带有一些距离,转而向往远方的世界。我尽可能不做任何修饰,不去操弄或加以组合,让原色的声音直接排列, 然后仔细地观察看看。通过这样的方式,我的崭新音乐也将逐渐成形。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音乐即自由》,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
下一篇:卅年翰墨愈精神
大家都在看
-
20根肋骨同时折断?揭秘人类分娩为何最痛 哎呀,姐妹们,今天咱们聊点扎心的。生过孩子的都懂,产房里那滋味,真是谁生谁知道——宫缩一起来,就跟肚子里的零件被重新组装似的,疼得人恨不得抓着床头做引体向上。没生过的可能也听过那句“相当于同时折断20根 ... 人类之最12-18
-
雅尔塔会议的位置不是随便坐的,谁的地位更高,贡献更大一目了然 1945年雅尔塔那张合影,斯大林为何乖乖坐侧边?只因罗斯福身后那张天价账单一九四五年2月,克里米亚的寒风里,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会议刚散场。作为东道主,那个被称为“钢铁之人”的斯大林,竟然乐呵呵地坐在了侧座 ... 人类之最12-17
-
教育孩子应该了解的世界之最 教育孩子应该了解的世界之最了解“世界之最”是孩子们认识世界、拓展视野的绝佳方式。这些记录不仅有趣,更蕴含着地理、历史、生物和科技等多学科知识。以下为您梳理了多个领域的“世界之最”,帮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 ... 人类之最12-15
-
他一生没写过字却用马蹄在欧亚大陆刻下人类史上最庞大的标点符号 成吉思汗:一位以草原为稿纸、以铁骑为刻刀的文明断句者1206年,斡难河源头。九脚白纛猎猎作响,风卷起苍狼图腾旗上未干的血渍。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意为“海洋般辽阔的君王”。可真正震撼历史的,并非这个 ... 人类之最12-15
-
人类最珍贵的品格是什么? 探寻人类最珍贵的品格:照亮心灵的璀璨之光在人类文明的漫漫长河中,无数品格如繁星般闪耀,它们构成了人类独特的精神世界。那么,人类最珍贵的品格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善良——温暖世界 ... 人类之最12-13
-
一曲霓裳尽风华 京剧包拯脸谱川剧包拯脸谱秦腔包拯脸谱昆曲《牡丹亭》生媛媛扮演杜丽娘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中指出,“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瑰宝,既指奇珍异宝,又指珍贵的精神财富,还指能 ... 人类之最12-12
-
成吉思汗不是只会射雕的猛男而是人类史上最牛的创业CE0 那个让欧洲人听见名字就哆嗦、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上帝之鞭”的男人:成吉思汗!骑着蒙古马、弯弓射大雕 一路狂飙灭国四十个打到多瑙河边,吓得教皇连夜写信求和他靠的是一套超前800年的管理系统+人才机制+品牌营销+ ... 人类之最12-12
-
以军枪杀跪地投降者,内塔尼亚胡“最道德”言论,沦为国际笑话 “全世界最有道德的军队”,我以前差点就信了,直到看见那段让人心脏骤停的视频。那两声枪响,撕碎了什么那段视频,没有任何配乐,画质也谈不上高清。但它带来的窒息感,比任何恐怖片都真实。两个巴勒斯坦年轻人,面 ... 人类之最12-09
-
华沙之跪:那一刻,唤醒人类良知的深沉忏悔 在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画面,往往不是华丽的辞藻,也不是强烈的口号,而是那些发自内心、用行动表达的真诚。二战的阴影还未散去时,欧洲的土地上弥漫着仇恨、痛苦与沉重的记忆。而在这些记忆中,有一幕,像一束穿透 ... 人类之最12-08
-
爱情之花——永恒的主题,人类最宝贵最灿烂的灵魂绿宝石 她曾迷恋丈夫的浪漫和激情,一场重病让她明白:激情型爱情是婚姻的滑稽戏。晓月把药片丢在床头柜上,发出清脆一声。她终于明白了,电影里的爱情都是骗人的,那些轰轰烈烈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誓言,在婚姻里只剩下 ... 人类之最12-07
相关文章
- 华沙之跪:那一刻,唤醒人类良知的深沉忏悔
- 揉耳通经络!大雪节气养生从头暖到脚
- 爱情之花——永恒的主题,人类最宝贵最灿烂的灵魂绿宝石
- “人类最惨一年”是哪一年?公元536年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 南京大屠杀:三十万冤魂的泣血呐喊,揭开人类文明最黑暗一页
- 华沙之跪:一位德国总理的忏悔与人类良知的呼唤
- 【人体奥秘04】大脑:你那1.5公斤重的“宇宙”
- 人体:宇宙间最精密的智能体
- 篝火旁的裂痕:人类社会最初阶级的诞生之路
- 人类历史上非常烧脑的5大悖论,你曾考虑过这些问题吗?
- 孔子最伟大的思想是什么
- 人类与AI的“终极屏障”,或许就藏在“此时此刻”
- 人类战争史上最离谱的5次翻盘,第4个像开了挂
- 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艺术史上最动人的慈颜
- “数学之王”高斯:天才少年如何用智慧改写人类科学史?
- 稻粟之歌:粮食之祖的种植与传承,书写人类生存的诗篇
- 这项人类最不起眼的一种能力,却是AI永远的短板?
- 这项人类最不起眼的一种能力,却是 AI 永远的短板?
- 凡尔登战役:毒气、炮弹、绞肉机——人类历史上的血腥炼狱
- 字里行间的奇迹:人类文明的“符号”狂想曲
热门阅读
-
关于男人的15个世界之最,最长阴茎达56厘米 07-13
-
东方女性最标准的乳头(图片),看看自己达标吗 07-13
-
人体器官分布图介绍 五脏六腑的位置都在哪 07-13
-
木马刑是对出轨女性的惩罚 曾是满清十大酷刑之一 07-13
-
熙陵幸小周后图掩盖性暴力 至今保存于台湾博物馆 07-13
-
包头空难堪称国内最惨案件 五名遇难空姐照曝光 07-13
-
2022中国最新百家姓排名,你的姓氏排第几? 03-26
-
好玩的绅士手游有哪些?2022十大绅士游戏排行榜 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