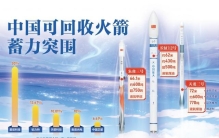仲伟民X马俊亚X孙竞昊:大运河悲喜剧下的明清社会图景
区域社会经济史是当今历史研究中重要且日益受到更多关注的领域。而在区域历史的研究中,江南、岭南地区尤其受到国内外学界关注。但历史上的这些区域,在日常生活、经济发展等各个维度能否代表中国的大多数区域?这是近年来区域史研究领域“走出江南”理念的一个问题意识。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孙竞昊的新著《经营地方》正是对“走出江南”理念的实践,通过立足大量一手文献,梳理了济宁城市自明末清初至开埠以来的历史演变。《经营地方》通过对济宁城市化道路、城市形态、社会属性、文化认同及政治变革取向进行的全面分析,揭示了一个北方运河城市与江南城市发展的不同路径。
在济宁城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除了《经营地方》中强调的地方士绅力量的推动,作为大型国家工程的大运河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不过,有区域因水而兴,亦有地区因水而衰,淮北地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淮北出身的学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俊亚的《被牺牲的“局部”》正是国内关注这一问题的典范之作。在当今人们的印象中,“淮北”地区常常被视为一片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内陆区,但根据中国古代的诸多史书记载,这片区域常以富足的形象出现。“淮北”面貌的“乾坤大挪移”与不合理的政策执行息息相关,马俊亚指出,中央政府的“三大政”——漕务、河务、盐务有相当大一部分集中于淮北区域,而大运河河务给这片区域的人民带来的更多是沉重的负担。
明清以来,包括淮北地区在内的广义华北社会发展,究竟受到了哪些主要因素的影响?区别于经济、文化中心的明清江南,淮北、济宁地区的人群结构经历了怎么样的演变?地方社会人群对外部压力如何应对与选择?地方士绅与朝廷力量如何博弈与互动?
“淮北”和“江南”,
哪个更能代表中国大多数的区域?
仲伟民:大家知道,最近20年,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非常热、且成果做的也比较深入的一个领域就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江南研究、华南研究等。孙老师在江南研究方面做得也非常深入,他师从王家范先生、谢天佑先生。我们也很期待未来他有关于江南的精彩论著出版。
不过今天要谈的这本《经营地方》并不是着眼于江南,而是涉及济宁地区。但我个人可能更喜欢这本书,这也和我这几年对华北历史研究的关切有关,而且我个人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华北核心区,当然,这个概念现在还有争议。马俊亚老师的《被牺牲的“局部”》和孙竞昊老师的《经营地方》,所写的地区虽然不是重合,但其实是相关的,所以我认为,大家可以把两本书拿来对读,应该会很有收获。
孙竞昊:谢谢伟民兄!这本《经营地方》是我的第一本书。我的老师谢天佑先生一辈子也只完整地写了一本书,《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还有半部遗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谢先生跟我说,如果你用一篇文章就能把思想表达清楚了,就没必要弄出一本书来。我的第二位老师王家范先生,除开论文集,一辈子也只出了一本书,《中国历史通论》。老师们都对我影响比较深。还是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督促,让这本书能够顺利出来。很多人问这本书为什么起《经营地方》这个题目,我们知道罗威廉有本很有名的书叫《救世》。他强调国家,而我强调“地方”,所以他的书名是“Saving the World”,我就叫“Managing the Local”。基本上这本书脱胎于20年前的博士论文,里面一半的内容是我的学生们帮忙翻译的,他们尽了很大的努力。如果读者们发现了一些不满意之处,我本人负全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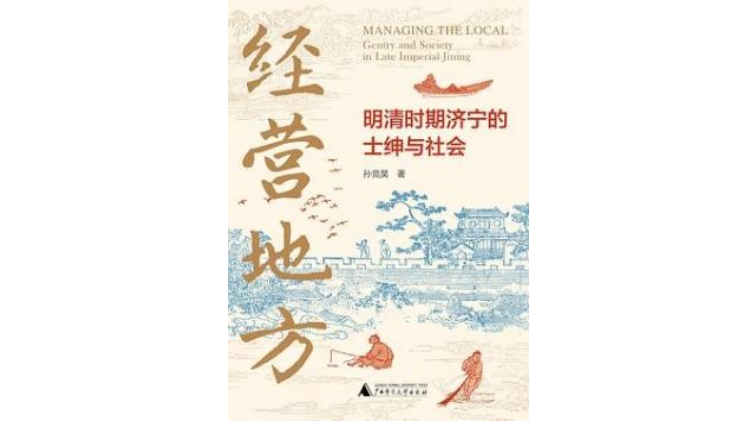
《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孙竞昊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 2023年3月。
仲伟民:谢谢孙先生。马老师的《被牺牲的“局部”》现在也基本上是区域经济史研究领域“名片”式的作品,也想请马老师谈谈自己写作这本书的经历。
马俊亚:谢谢!《被牺牲的“局部”》写的是我们国家淮北地区的历史,我的老家江苏沭阳县也属于这片区域。20世纪80年代我出去读书的时候,苏北有两个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就是我们沭阳,另一个是灌南县,整个苏北地区都是不发达的,现在可能大家还是有这种印象。当时我进苏州大学就读时学校里流行交谊舞,我印象中一到周末大家都去跳舞,苏南的同学很多,穿得也比较漂亮,我则是一年四季可能有三季都穿同样的衣服,因此不大去跳舞。当时甚至电影都不怎么看,整个大学就没什么“奢侈”的消费。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去图书馆看书。
就是在看书的过程里,我逐渐产生了很多困惑。比如我发现,《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里面,我们所谓“贫穷落后”的苏北地区其实是不落后的,“十三经”里面它是一片很好的地方,淮河流域在唐以前甚至完全是一个鱼米之乡,但到了后来我们谈鱼米之乡,基本上都会认为是太湖流域,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如果说中国历史是4000年历史长河,那苏北地区在历史上至少领先过3000年,当然,这个领先是用农业文明的标准——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水平——来看的。而相对的,江南地区反而是落后3000年,领先1000年。这其实就引起我一个苏北人的兴趣:苏北和苏南经济地位的这种“乾坤大挪移”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后来我读研究生到读博士,做博士后研究,其实一直做的都是苏南地区的研究。我想,把苏南地区观察研究完一遍后,再去回看苏北,可能要看得更客观一些。做区域研究,我们不能就一个地区研究一个地区,这样视野容易闭塞,也说不清楚一些事情。虽然我学术生涯的前20年基本上都在研究苏南,但到苏北的调查也很早就开始了。在苏北的调研经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调查累了渴了,看到一条河里的水是清的就直接捧一把喝了,晚上我就住在大澡堂里面,当时住里面的都是磨剪子的、卖爆米花的、耍猴的、卖糖葫芦的,什么人都有。可以说我在苏北做调研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观察者或者研究者,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生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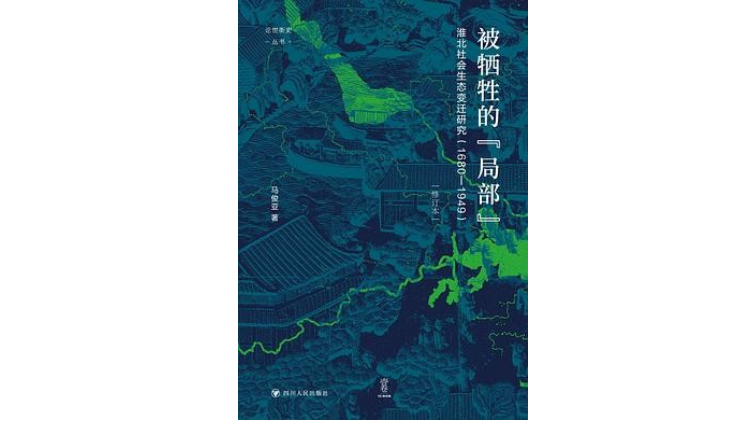
《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马俊亚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YeBook 2023年2月。
仲伟民:我刚才讲到这两本书有交集,这种交集不仅仅指地域上的交集,其实还有内容上的交集。这两本书都涉及一些影响中国历史十分重要的要素,比如大运河和黄河,马老师书里还提到了盐政。这里我想和孙先生交流一下,虽然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有些部分我并不是太同意,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经营地方》谈的是济宁,但我认为在华北地区,济宁是一个“非典型城市”,因为它的兴起完全是因为一些偶然因素,济宁之所以从元代到明清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实际上就是因为大运河。类似的城市很多,如果没有大运河,也不会有北边的聊城,甚至可能不会有今天的天津。我其实最有“意见”的,就是孙老师这本书的书名“经营地方”,我总觉得,这本书有很多地方都希望突出济宁当地的士绅对这个城市发展的这种“经营”作用。但相对于大运河的存在,士绅的作用是否这么大,我觉得有待商榷。
所以我认为,这本书里面最精彩的就是第一章、第二章,这两章恰恰就是在讲大运河对济宁发展起到的巨大影响。济宁发展的背后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力量的推动,而不是第四、第五章写的地方士绅特别地经营。这是我第一次和孙老师交流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其实也和马老师的书相关。刚才马老师讲到,淮河流域在唐代以前是鱼米之乡,的确如此,我们的很多历史文献都能充分证明这一点。整个淮北地区后来却转变为一个贫瘠之地,有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人为的、封建政治的因素,而大运河的影响就不容忽视。这里也想提一句题外话,我个人认为在目前中国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像刚刚提到的江南、华南研究,都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研究非常多,尤其是江南地区,非常受到海外学界的重视。他们甚至会把中国的江南视为中国区域的代表,比较典型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大分流理论。这是我认为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我经常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我觉得真正比较能代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恰恰是淮北这类区域。
孙竞昊:谢谢仲老师!这个质疑非常合理,我当时也考虑过。在运河方面,我和俊亚教授的看法确实不是特别一样。当年我们都看过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里面有一句台词是说:“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我个人觉得我们在研究局部的时候,还得跳出局部,去看一个更大范围的区域。当然马老师是跳出来了的,他说大运河不但让淮北被牺牲了,国家也没有得到很大的好处。不过这其实也不是马老师的独创,毕竟利玛窦、魏源都曾这么讲过。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维持这个运河?我觉得这需要纳入到整个大国的政治经济版图里去看。
刚刚仲老师说,没有国家的力量,济宁就还是一个一般的州或县,包括临清、德州。在城市化道路方面,它基本上确实是一个从外部输入的过程,像后来的深圳一样,是国家决策的结果。但临清科举很差,后来遭到王伦起义的打击、近代化的打击,就慢慢边缘化了。那么济宁后来为什么没被边缘化?首先就是它的科举是山东做得最好的几个之一。其次,大运河后来衰落了,这给沿线很多城市以影响。我们知道有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现在路没了,济宁当地的士人和他们在北京的京官就搞了个保路运动,修铁路。到了19世纪后半叶,济宁超过了临清。这里面能看出一些地方精英的力量。
这里也插句题外话,李泽厚先生曾谈到过所谓“片面的深刻”,如果一个书写得非常中庸,既不肯定又不否定,就陷入了所谓“庸俗辩证法”。我觉得马俊亚老师这本书在风格上是比较“Sharp”的,我这本书在观点上就会显得“中庸”一点。

对谈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马俊亚、孙竞昊、仲伟民)
大运河的“喜剧”与“悲剧”
仲伟民:我觉得孙老师未来可以做一个比较研究,从科举来讲,聊城的科举的比例好像也不是太低,当然临清可能要差一些,可以找一些数据,再探讨探讨地方士绅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到大运河,现在大运河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重点宣传的历史文化遗产项目。它当然算是一个文化方面的成就。但我们也要客观地从历史角度看它对淮北、山东沿岸这些地方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孙老师和马老师的两本书都花了很大精力讨论运河,我觉得其实一本讲的是“喜剧”,一本讲的是“悲剧”。《经营地方》可以看作一出大运河的“喜剧”,因为没有大运河就不会有济宁城的繁荣。但《被牺牲的“局部”》完全不一样,它说的是当时封建朝廷为了保证大运河的畅通,实际上把整个淮北地区牺牲掉了。
这也和宋代以后整个中国大的局势有非常大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从汉唐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关中,然后东移到中原地区,可到了宋代,经济重心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而这个变化,其实又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所谓当时的国际形势就是宋、辽、金、西夏)。在进入元代之后,封建朝廷把大运河列为重点的项目,就是为了把南方大量的资源调到北方,保证北方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地位。其实元代还好,因为元代相当多的年份都还利用了海运,运河发挥的功能比较有限。特别是在元代以后,朝廷可以说不计成本地保护大运河。也正是从明代开始,济宁城逐渐发展壮大,淮北地区却是越来越落后。
所以我常常想,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当时这种涉及国家命脉的大工程?实际上它不单单涉及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的兴起,而是和整体国家的政局相关。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味地去否定大运河,而是要回到历史的场景,做一个客观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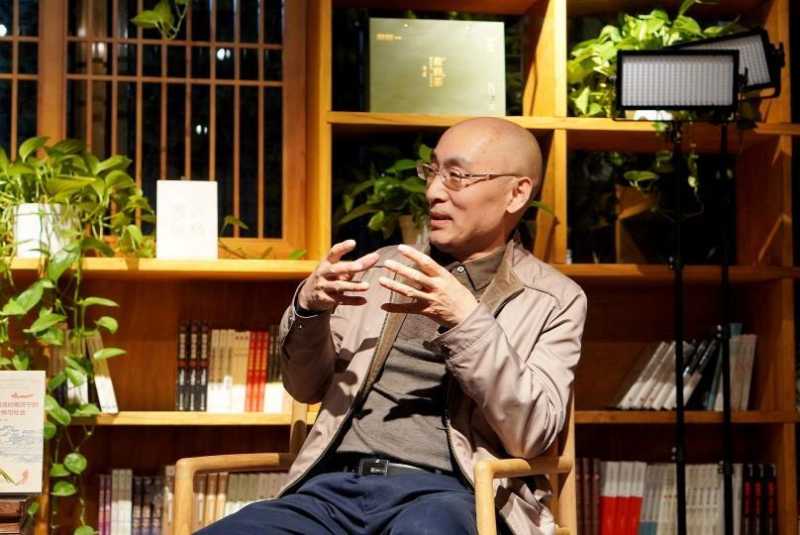
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常务副主编,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史学理论。
马俊亚:非常感谢仲老师。仲老师对我比较客气,对孙老师的书批得比较狠(笑)。但我还是想为孙老师的书说两句。我其实也觉得“经营地方”这个书名有些“中庸”了,很容易掩盖书中极具创新、非常普遍的亮点。书里有很多极具历史价值的学术思考,比如谈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所谓的商品经济,和学术意义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包括这些地方的城市化进程它和西方又是不是一回事?对这么多的概念和学界人云亦云的说法,孙老师从不落入前人窠臼,在这本书做了很好的辨析,并进行了非常前沿的学理性解读,正所谓二十年一剑。
当然,仲老师刚刚提到运河带来的一些弊病,我十分赞同。现在我们提到运河,很多人可能以为它是像长江一样,从高流到低,其实运河是所谓“三起三落”,是从一个屋脊上面走过来,再往一个屋脊上面走。运河的最高点实际上就是济宁附近这个地方,当时的说法是南旺分水。从南旺到临清地面高差是90尺,往南到镇口是地降106尺。所以济宁到我们苏北淮安一带,运河河床的落差有五六十米。这样运河进入山东境内就需要依靠一级一级的闸口把水保住。这就导致鲁南、苏北地区长期面临河水泛滥的情况。除了运河其实还有黄河,弘治年间刘大夏治水,几乎是把黄河全都推到了我们苏北地区。黄河水、淮河水也都从我们苏北走,这些都对这个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个人对苏北地区历史上河治不满意的另一点还有修水库。我们知道修水库一般要修在山沟里,这样不容易让土地被淹没。但洪泽湖是修在平原上的,而且只有东边一条坝。洪泽湖就是一个人工水库,每年为了保证漕船能过淮河、黄河,基本上三四月份开始蓄水,而整个淮北平原又没有什么落差,淮北地区基本上就都被水淹掉了。
刚才仲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也非常有意思。元朝的时候,尽管修了很多水利设施,但元朝的运河影响却比较小。为什么?因为元朝主要的漕粮是通过海运。我们知道,明清两代保运派比较得势,他们支持运河而不是海运的理由主要是海上有风险,风浪大,盗贼倭寇多。但仔细一想就会发现,这两个因素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海上风浪大,是人间地狱,那倭寇不也都被打翻了吗?如果海上到处都是倭寇,那说明海上没什么风浪嘛。而且更重要的是,明朝真正全面实行河运粮食的时候,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还在大洋里,你能贸然否定我们中国人民航海的成就吗?
所以其实明清两代官员,真要说保运,算的也是政治账,他没法算经济账,真算经济账就难说得过去了。清朝中期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4000万两银子。当时的漕运以魏源最保守的估算,一年运漕粮就得花掉1800万两银子。除此之外还得维修运河、黄河和高家堰等,经费大概每年是1000万两。更不用提整个运河的修建最终对苏北、皖北、鲁西南、豫东南生态的破坏,使得这个原本最为核心的区域成为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方。
所以,我赞同孙老师称自己的作品比较“中庸”。他书里写的那些观点非常对,运河对一些城市的商品流通、城市管理水平等等的提升是有帮助的。但这个积极影响可能主要是在沿运河的几个点,要是离开运河的中心区域,离开扬州、淮安、徐州、济宁、聊城、临清,到农村地区看,那些地方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就非常大,甚至是触目惊心的。
仲伟民: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我在课堂上有时候和同学们闲聊的时候也说起,必须保障明清大运河的畅通及其治理,很有可能是明清两朝最大的决策失误,这个决策失误说得严重一点,甚至带来了两个封建王朝的衰落。这个决策对大运河沿岸,尤其是从鲁西南往北,重点是在四省交界的这些地区影响尤其大。这也是我们目前做环境史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也应该对大运河的作用作出一个客观的评价。它确实带来了一些大城市的兴起,也带来了诸多地区生态、经济的破坏。
回到济宁,其实济宁是在大运河衰落之后,经历短期的经济回落,又迅速反弹,发展至今成为山东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可能仅次于济南、青岛、烟台。我想,如果孙先生未来将这些发展背景考虑进去,这本书的内容应该会更加完善。
孙竞昊:非常感谢二位。不过这本书应该算是翻篇了,不会再有太多修改(笑)。我会在即将完成的英文专著里考虑马老师说的这些问题,讨论运河对周边地方的影响。写这本书,其实主要还是和我对济宁本身的问题意识有关。我们知道,在美国学术圈,知道济宁的人寥寥无几。那么大家都会问你为什么要研究济宁?它的特殊性在哪里?
我在自序里提到过,我写济宁有几个不同层面的想法,除了史学的,还有方法上的,我想展示济宁作为北方典型运河式城市的特征。前年我去济宁,他们文旅部门开会,说该怎么宣传济宁,因为大家感觉到山东都去曲阜、济南、青岛,不去济宁,得想个口号。他们后来想的口号就是:世界的济宁。我给他们的建议是,“一个北方的南方城市”。济宁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特点,很文质彬彬,像南方的城市,就连当地的咸菜都是咸中带甜的。
最后我想通过济宁研究得出思想层次,就是济宁怎么样演绎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就是士绅的作用,这显示出了济宁和临清、德州等北方运河城市的不同。至于我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还需要诸位来评判。仲老师对我一直是“鞭策为主”,我也很感谢他的“鞭策”。

孙竞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明清时期区域环境、经济、社会史(侧重江南和华北)及其近现代变迁。
淮北士绅与江南士绅,
在地方发展中扮演怎样不同的角色?
读者提问1:我来自山东淄博,我想向老师请教的问题也与我出身的地域有关,刚刚老师们提到了科举和士绅的问题。我在看县志的时候也见其中提到,“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我自己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所以我想请教的是,济宁包括淮北地区的士绅,自身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涵,在“经营地方”上和江南地区的士绅有什么不同?齐鲁的地方风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影响?
马俊亚:我抛砖引玉。很多研究都表明,江南地区士绅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兴修水利,到维护治安、漕粮征收满等等。这些地方的政府也有意识地把权力划分出来一部分交给地方士绅来做。包括东南地区那些小的纠纷,大多希望化解在地区内部。江南地方士绅也比较争气,整体上能让社会的行政成本变得很低。当然,江南地区士绅发挥作用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硬件条件:义庄。江南很多地方,义庄的土地能占到社会田地的10%,义庄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接济贫弱群体的福利性质机构存在。但反观济宁一带,其实士绅在地方起到的作用没法和江南相比。我记得周锡瑞写《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讲到济宁地区土地大户很多,但不接济穷人。我们苏北以前大的地主也很多,但也不怎么救贫,相反是靠苏南的士绅救济。
你刚刚讲到齐鲁地区男子“重农桑”。其实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不太相信一个地方的人选择去搞农业而不是从商,毕竟商业是最来钱的。过去在传统社会里面,如果有人不爱经商,其实往往不是因为这地区的人不爱赚钱,也不是缺乏“真金白银”。我们需要知道,在传统社会里,中国真正经商的第一要素是权力而不是资本。
读者提问2:之前看过马伯庸的一部历史小说《两京十五日》,里面讲到当年仁宗皇帝想要放弃运河,重启海运的时候,会遭到保运派的大批反对。除了刚刚马老师和仲老师讲过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沿岸大批的百姓都以此为生,如果废除漕运,会严重影响两岸人民的生活。但刚刚几位老师又提到,其实运河的存在本身就在严重损害一些农村地区百姓的生活。那么当地的士绅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有些矛盾的诉求?
孙竞昊:这个问题在马老师的书里谈得蛮多的。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非常清晰地揭示了很多漕政的弊病。我个人对这个看法并不是特别赞同,也是我和马老师不太一样的地方。我经常会跟学生讨论一个问题:我们真正了解自己吗?我们现在关于中国的话语其实受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封建”思潮影响非常深——皇帝就是极端专制,传统社会的官场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其实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中国的士大夫其实是以相互监督、揭露乃至批评皇帝政策为荣的。杨乃武与小白菜那么一个案子都产生了那么大的动静!我觉得中国的皇帝大多数也都是中规中矩的皇帝。他们最大的目的就是老百姓不造反,能交上税,就行了,并没有谁真的想对民众作恶。
马俊亚:我介绍大家看一个案子:甘肃冒赈案,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全省官员串通一气,地方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勾结舞弊,折收监粮、没一个官员举报,甘肃通省无一清官。当时有195名官员被查出来,这些官员按照清朝的法律都应该是杀头的,但乾隆当时不能全杀,杀了一部分。
我经常想起阿克顿勋爵的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我跟孙老师的看法相反,在中国古代,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人,不可能不腐败。如果回到这位读者提的问题,当时保运的人说运河为大家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失业问题,这里我需要提到明朝大学士丘濬的一个说法,就是当时海运的经费是河运经费的三至五分之一,如果把运河裁掉搞海运,我们能养十万海军,那海上盗贼不足为惧,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解决了海防问题。
运河解决就业的这个说法更不合理,我举个例子可能更好懂。比如秦始皇修长城,也解决了几十万人就业。但这个说法总还让人觉得很奇怪。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里讲过这样一段话,直接的强制劳动就是奴隶制。修运河的人是被强制劳动的,他们是劳动奴隶。是统治关系,而不是资本劳动者变为奴隶。
马克思讲人的自由发展,其实就是不能让人活在一种强制劳动关系之下。就像恩格斯说美国种植园里面的奴隶的生活可能都比当时欧洲工人的待遇好得多。就算一个人富裕了,解决了生计问题,但没有自由,那还是奴隶。

马俊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区域社会生态史。
读者提问3:我跟马老师算是同乡,我家是宿迁的。虽然我和马老师年纪相差比较远,但还是会感到自己的家乡有那种经济和文化上落后的感觉。另外我自己现在也在做晚清政治和人物研究,但我发现在历史材料里面,我的家乡经常是一个边缘地带。我看官员的日记,他只会在“途经”宿迁的时候,才会提到这个地方,但他并不会在这里停留。老师刚刚也提到,苏北地区出过很多大的地主,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后代没有通过科举完成阶层上升,实现一种文化的向上输出,并且让这个地方获得中央政府的关注呢?
马俊亚:谢谢这位老乡!这个问题其实也比较简单。我们知道江南地区比较强调耕读传家,这里倒确实像是孙老师说的,出清官的地方。以前我们经济史领域的鼻祖级学者陈翰笙曾经对苏南、苏北都有研究,他说苏南的地主一般就是三位一体:地主、商人、资本家,赚了钱就去买地,那样买的地是很零碎的,10亩、20亩,能买个100亩就已经是非常大的田地了。
苏北地主就不同,他们通常是军政地主,家里必须有司令、军长、督抚式的人物。这个我们看清朝反腐的档案也能看出来。他们买地经常就是3000亩、5000亩。这里面原因其实很复杂。刚才我讲苏北经常有水灾,它不像地震这种天灾,水灾其实是长眼睛的,更多时候是一种人祸。很多时候涉及淹哪边不淹哪边的问题。咸丰年间微山湖一蓄水,大家只能逃荒,官府就把数百万亩的田地卖出去。所以苏北很多地主不是通过江南那种商业合法渠道,而是用权力兼并土地成为地主的。权力又是很容易被取代掉的,和珅被查处了,那下次来水,肯定就淹没他们家,别人就取而代之,根本不需要考科举,考科举对这个地方来说来财太慢。所以这可能导致苏北这块地方不是特别重视科举文化。另外我刚刚讲到南方的义庄,从小就有培养读书的传统,有书院,北方比较少。
孙竞昊:我插一句话,刚才其实仲老师还有马老师其实都谈到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我想说的是,历史和现实是有连续性,但也不是一定一样的。做历史要有情怀,就像仲老师、马老师,他们的作品都有情怀,但是历史和现实不是一回事。所以我在“澎湃”发的一篇文章就讲过,我们既不要被历史“俘虏”,也不要被现实“俘虏”。
整理/刘亚光
编辑/申璐
校对/李立军
大家都在看
-
《最高明的活法:看清所有规则,为真实"饥饿"买单》 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深夜刷着手机,对一款标价不菲的“故乡味道”预制菜心动不已。你清楚地知道,那包真空料理与童年灶台上的烟火气相距甚远。你一边嗤笑商家的情怀包装,一边默默点击付款。这看似矛盾的行为, ... 商业之最12-20
-
当下最赚的9种生意!全抓人性痛点 当下最赚的9种生意!全抓人性痛点打开手机刷购物软件,刷短视频看直播,你是不是总忍不住下单?其实不是你管不住手,而是现在的生意都精准拿捏了人性!不管是城市白领还是小镇青年,不同人群都有专属的“消费软肋” ... 商业之最12-20
-
汉阳人民集合!25万方巨型商业体,你最期待什么品牌? 汉阳的父老乡亲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我们自己的巨型商业体——金茂览秀城,全球招商已经启动啦!这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决定未来家门口能逛到什么、吃到什么!据说项目重点引入的是国际潮流品牌和沉浸式体验业态, ... 商业之最12-20
-
行业观察 摘 要恒丰银行更大的蜕变在于将金融资源向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倾斜:近年来,全行八成以上存量贷款投放在沿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坚持“做强本土”战略,全力服务山东“走在前、挑大梁”,承销山东 ... 商业之最12-20
-
商业合作最稳的底层逻辑:把信任检验做到位,少踩80%的坑 商业里所有“合作翻车”的闹剧,本质上都是信任的崩塌——要么是对方能力撑不起承诺,要么是人品经不住利益考验。我们总容易被饭局上的“情投意合”打动,聊几句共同观点就觉得找到了“灵魂合伙人”。但口头上的共识 ... 商业之最12-20
-
擦边主播们,把小红书变成小“黄”书 小红书正面临一场微妙的身份危机——当深V睡衣主播与"陪叔叔谈心"的标题频繁出现在推荐流,这个以女性用户为主的生活方式社区开始显露出"擦边"生态。本文深度剖析平台在用户增长与社区调性之间的博弈,揭示从7:3性别 ... 商业之最12-20
-
商业炼金术:当人性成为当代最畅销的商品 互联网时代,最好的生意不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一场场精准的“人性方程式”求解。一句广为流传的话道破了玄机:“向少年卖娱乐,向少妇卖仁波切,向老妇女卖青春……”但这条商业逻辑链在2025年的今天已经进化得更长 ... 商业之最12-20
-
网红直播翻车,品牌方秒切合作,背后的商业逻辑让人深思 这事儿真是来得突然,合作说黄就黄了,让人看了都觉得挺惋惜的。那家食品公司动作倒是很麻利,转眼间就把所有相关的宣传物料都给撤了个干净,生怕自己也被卷进去。企业在商言商,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名声 ... 商业之最12-19
-
中国可回收火箭“压轴”12月 商业航天蓄力突围 2025年是中国的商业航天事业从技术积累走向爆发的一年。这一年,多型号民营航天企业完成火箭发射试验,随着卫星互联网组网加速,商业逻辑逐渐清晰,多型号新型火箭的研制节奏已全面按下快进键。同时,政策红利在这一 ... 商业之最12-19
-
管仲:从阶下囚到千古一相,如何用商业头脑成就春秋首霸? 春秋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的街道上,商贾云集,各国货物琳琅满目。在这繁荣景象的背后,站着一位身穿丞相官服,面容清癯的中年人——管仲。他既非出身贵族,亦非饱读诗书的儒士,却凭着一套颠覆传统治国理念的“经济战 ... 商业之最12-19
相关文章
- 中国可回收火箭“压轴”12月 商业航天蓄力突围
- 管仲:从阶下囚到千古一相,如何用商业头脑成就春秋首霸?
- 上海最富的三个区:黄浦静安徐汇,藏着怎样的房价与圈层秘密
- 中国可回收火箭“压轴”12月 商业航天迈入爆发期
- 王兴不是企业家,他是中国商业史上最清醒的「现实语法解构师」
- 怡和集团:从鸦片贸易到跨国巨擘,穿越近200年的商业浮沉
- 我的脸,是他最失败的商业并购
- 这个“少年烤鸡”用双手撬动成人世界的商业规则
- 你的欲望是否正在被商业精准收割?揭秘消费背后的“人性陷阱”
- 价格演义
- 零售额、客流同比增长超30%,在上海“最卷”商圈,这家商业体凭啥脱颖而出
- 击穿行业天花板:马斯克的万亿商业局
- 范保强:商业传奇中的“五无”标杆—解码一位企业家的责任与坚守
- 做好商业提质“必答题” 以场景之新创生活之美与增长之实
- 《道德经》被误读最深的一句话:弱者道之用,才是真正的顶级智慧
- 从6亿到24亿订单爆发!航天电子押注商业航天,散户理性布局攻略
- 《大生意人》---爽文滤镜下的商业幻梦。
- 4倍暴涨封神!牛散张素芬死磕亏损股三年埋伏挖出商业航天垄断王
- 杀疯了,大模型第一股花落谁家?
- 从10元到40元!商业航天4倍牛股背后,11家唯一龙头撑起万亿赛道
热门阅读
-
世界上最小比基尼,几根绳子也能叫比基尼 07-14
-
胡文海事件真相,以暴制暴杀了村干部等14人 07-14
-
好日子香烟价格,多款不同系列价格口感介绍 07-14
-
缅甸惊现最古老琥珀 距今一亿年价值连城 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