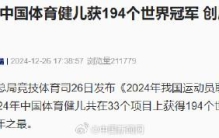19世纪,在美国废奴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之间,谁更有权利优先权?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1840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收到世界反奴隶制大会的邀请函之后,派出了代表团前往伦敦,其中有男性代表也有女性代表。
女性代表是“在加里森的鼓励下由三个女性反奴隶制社团所推选的,她们漂洋过海来参加会议”。

当时的英国反奴隶制协会以及与会的其他美国代表团一致认为派遣女性代表出席会议是荒唐之举,女性代表的出现引起了现场的巨大轰动和强烈争议。
于是,大会的第一项议程并不是关于奴隶制,而是变为会议参与者通过辩论和投票来表决是否能接纳女性代表。
辩论的双方都认为,此时此地讨论妇女权利问题并不适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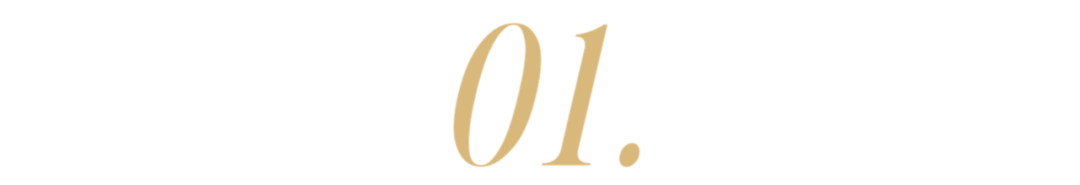
一、妇女权利与废奴事业的冲突
来自伯明翰的代表约翰·安杰尔·詹姆斯在提到最近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分裂时,声称妇女权利的提出对废奴事业来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而这个问题本应在美国就得到妥善解决。
他称妇女问题是对废奴事业“令人讨厌”的干扰。双方都没有谈到女性是否有资格、有经验或有能力参与辩论。

这些代表主张把重点放在废除奴隶制上,这一策略是为了避免妇女问题与会议上要解决的平等、正义问题捆绑在一起。
英国浸礼会牧师查尔斯·斯托维尔说:“难道我们不是承诺要牺牲一切,以便我们能做一些反对奴隶制的事情吗?我们要不要在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让整个仁爱的浪潮被一根稻草所阻挡?”
他立即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大声说:“不!你说要做男人,那就做男人!考虑清楚什么是值得你关注的”。
这场辩论完全展现了传统观点:虽然应该赞扬女性的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但允许她们参与辩论将会侮辱女性应该在私人领域中行动这一传统。
而这种被称为“私人领域”的概念,在历史上一直是女性次要地位的基础。

结果,90%的男性代表反对让女性代表就座,认为接受妇女不仅违反了英国的传统,也违反了上帝所规定的条例。
此后,在男性代表可能认为是宽宏大量的姿态中,大会禁止妇女代表参加会议,强迫她们坐在帘幕之后,远离其他代表的视野之外,安静旁听而没有参与讨论发言的权利。
只有到晚上,当围坐在旅店的餐桌旁,她们才能参加与男性代表们的辩论。
美国妇女代表并没有对事态的发生和转变感到太惊讶,会议上对妇女的看法与几个月前美国反奴隶制协会上所暴露的偏见相似。
尽管以温德尔·菲利普斯为首的支持者在会上发言维护妇女权利,但他们以陈旧的女性形象来描绘在场的妇女,依旧无法克服自己的偏见。
此外,男性拒绝让女性发言,认为自己能为女性发声。这一行为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家长式的态度,即把妇女定义为屈从于男人,不能为自己说话。

这种态度加强了妇女在十九世纪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这场为了打破奴隶制的枷锁和镣铐而召开的会议,允许在场男性以妇女为代价享受权利和特权。
根据后来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回忆说:“当时,菲利普斯向大会保证,这些妇女无论是坐在帘子后面还是获得席位,对大会内容的感兴趣程度是一样的”。
斯坦顿说,这番话显示出大会代表根本无法理解女性的情感。后来,她质问菲利普斯:“是否当黑人被拒绝入席时,你也会这样麻木不仁”?
菲利普斯和斯坦顿是彼此尊重的朋友,但他们的争论表明了废奴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从一开始便已存在的紧张关系。
当黑人男子权利和妇女权利之间面临艰难选择时,冲突的爆发便无可避免。
尽管他们作为废奴主义者,他们与教会作斗争来证明黑人的自由权,“但出于理智,他们禁止将这些神圣权利的界限延伸至妇女,给她们平等和自由”。

正是世界反奴隶制大会上发生的这样讽刺性一幕,使得妇女权利领导者开始提出她们的一个基本原则:男性不能为女性说话。
正如朱莉娅•伍德所解释的那样:“不能指望当权者有效地表达边缘化群体的经历,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等级地位方面的既得利益”。
玛丽格·格鲁作为被排除在世界反奴隶制大会之外的女性之一,她“回到宾夕法尼亚州后开始传播《已婚妇女财产法》的请愿书。
她的废奴主义者父亲曾积极鼓励她为奴隶做类似的工作,但他强烈反对为妇女做这些事情”。
而另外两位女性代表在会下讨论了自己的尴尬处境,她们认为除去完成解放黑人奴隶的目标外,另一项当务之急是追求女性自身的平等权利。

这两名代表便是后来美国第一次妇女权利运动的发起人:卢克丽霞·莫特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在世界反奴隶制大会上,她们分享了彼此对妇女被排斥在外的愤怒。根据斯坦顿后来的描述,她和莫特就是在那里决定回国后组织一次讨论妇女权利的会议”。

二、改革的首要目标
在1848年塞涅卡福尔斯大会上的首次演讲中,斯坦顿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妇女必须自己做这项工作;因为只有女人才能理解自己堕落的深度。男人不能为她说话”。
通过废奴运动中两场重要的会议和代表的反应,我们不难发现,在19世纪30和40年代的美国政治环境中,争取黑人权利是当时改革者的首要目标和依托。
对废奴组织的依赖影响了这一时期对妇女权利的提出和追求,争取妇女权利只是少数群体的目标,它是分散的、不成规模的。

提出争取妇女权利被认为是在转移争取黑人权利的注意力。此外,就算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明确支持妇女权利斗争的加里森派,也有其保守的一面。
一方面,他们试图打破政治参与中的性别和种族框架,使白人妇女和非裔美国人能够充分参与政治辩论。
另一方面,加里森派依旧在19世纪政治的框架内运作。他们用女性操持家务的感性形象来加强对奴隶妇女繁重劳动的谴责。
“如果说受害妇女的例子更能引起人们的同情支持,那么黑人男性奴隶的例子则能更有效地要求正义。如果说妇女应该得到在奴隶制下无法得到的保护,那么男人就应该得到权利”。
加里森派在提出这些主张时,利用了传统观念中对妇女的印象,损害了妇女权利领导者对妇女解放的呼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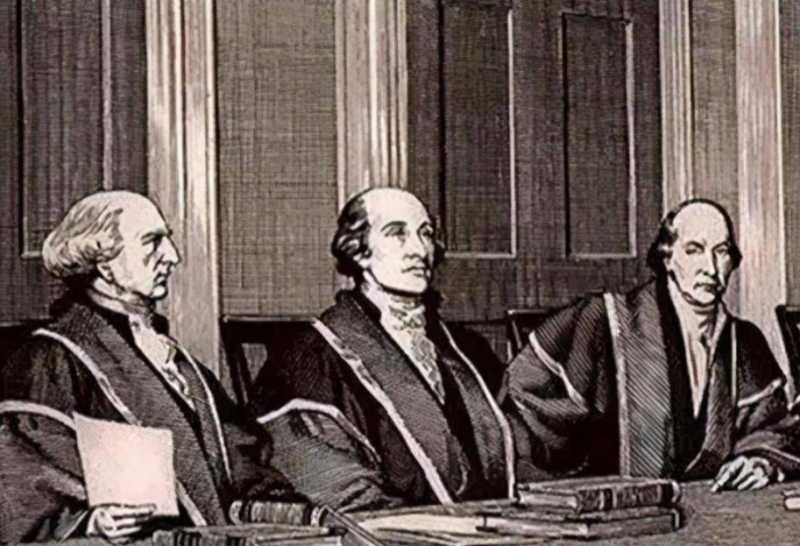
由于加里森派废奴主义的激进主张和表现常常与当时社会的主流认同相违背,因此在公众中的号召力不高。它也不再是妇女权利运动最能依赖的土壤。
而两次会议上的经历时刻警醒着妇女权利领导者:当抗争政治兴起的时候,她们的性别是被排斥在政治权利之外的。
这也导致她们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支持妇女选举权,以此来消除性别作为政治特权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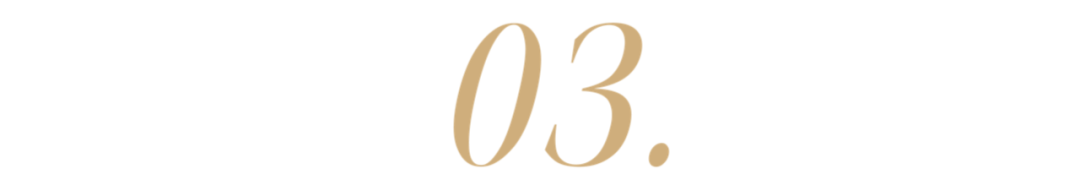
三、独立的妇女权利运动
随着1848年塞涅卡福尔斯大会的召开,一个独立的妇女权利运动诞生了,它将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美国政治文化中。
19世纪的妇女权利运动基本上是一场由白人中产阶级妇女领导的运动。虽然理论上同情贫穷的工人阶级妇女,同情黑人、亚裔、西班牙裔和印第安人等等。
这种中产阶级妇女权利运动主要致力于妇女选举权,对其他妇女具体的经济需求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妇女权利运动产生于一个相对废奴运动而言较小的男女群体,他们在美国公共生活中表达了高度的理想主义,并且这种理想主义在运动中延续。

因为妇女权利领导者植根于自己的社会,所以她们和人类家庭中的其他人一样都是不完美的人。许多白人妇女参政论者正在采取一种“权宜之计”。
她们愿意以牺牲黑人男性的利益为代价,安抚自己阵营中的亲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及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
在19世纪中后期妇女权利与黑人权利优先权博弈中,白人妇女权利领导者反复强调:如若黑人女性依旧无法获得自己的权利。
那么同种族男性就会成为她们的主人,情况便和未废除奴隶制前一样糟糕。
争取黑人女性的权利本质上依旧是为了满足白人女性的需要,这也意味着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很难打破种族主义的壁垒。
妇女权利领导者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也最终阻碍了19世纪中后期性别和种族平等的真正实现。

而废奴主义者把黑人权利放在妇女权利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男子至上的偏见。
他们在没有给予妇女权利的情况下提出黑人男子权利的要求,是对当时白人男性构建的政治结构的妥协。
在争取女性选举权和黑人男性选举权的激烈斗争中,这些领导者有时会成为普遍存在的男性至上主义观念的牺牲品。
他们认为女性权利可以通过她们对男性的自然感情得到间接的体现。如果黑人男性获得了选举权,那么黑人女性也将获得这种间接代表权。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不公正的种族状态和社会关系安排下,男人和女人的利益存在矛盾和对立。
废奴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一样,不可能脱离种族、阶级、地区和文化意识而独立存在。这两个少数群体之间权利优先权的演变也说明了当时社会改革的艰难。
大家都在看
-
创历年之最!2024中国体育健儿获194个世界冠军 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26日发布《2024年我国运动员取得成绩报告》。2024年中国体育健儿共在33个项目上获得194个世界冠军,数量创历年之最。 体育之最12-29
-
2024中国体育健儿获194个世界冠军 创历年之最 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26日发布《2024年我国运动员取得成绩报告》。2024年中国体育健儿共在33个项目上获得194个世界冠军,数量创历年之最。(央视新闻客户端) ... 体育之最12-29
-
中国跳水队有“十大之最”,你知道都有谁吗? 第一最,历史之最 - 郭晶晶她在跳水生涯中多次征战奥运会等重大赛事,斩获多枚金牌,其辉煌成就成为中国跳水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期统治女子跳板项目,是跳水界的标志性人物,见证了中国跳水的一个辉煌时代,众 ... 体育之最12-25
-
首届滑冰马拉松挑战赛来啦,这一次还将带来三个“之最” 1月30日至2月3日,首届中国·吉林松花江滑冰马拉松挑战赛将在吉林省靖宇县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举办。而江上滑冰马拉松,在国内也是首创。 省体育局副局长刘琦介绍说,本次滑冰马拉松也将创造三个“之最”。一是国内 ... 体育之最12-16
-
2020年,北京女孩为配合拍摄,从2500米高空一跃而下,已离开4年 源自真实案件,案中人名为化名资料来源:北京晚报《翼装飞行失联女生最后一跳画面》声明:作者原创文章,无授权转载抄袭行为一律追究到底!“天门山?安安,你怎么会想去那里啊。“天门山?安安,你怎么会想去那里啊 ... 体育之最12-11
-
2024年厦门中小学中职学生田径锦标赛闭幕 破纪录数创历届之最 厦门网讯(本网记者 马庆伟)11月30日,经过四天的激烈角逐,2024年厦门中小学中职学生田径锦标赛圆满地完成了各项竞赛,在厦门体育中心田径场顺利落下帷幕。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全市47所学校共计1191名运动员参赛, ... 体育之最12-11
-
中国田径史之最十个 ·王军霞,保持世界纪录最久,最多30年。·姚明,历史地位最高,大满贯。·刘虹,世界冠军。·孙彩云,破世界纪录。·徐永久,最早,最多30年。·陈跃玲,奥运冠军。·杨传广,最早,最多30年。·郑凤荣,保持世界纪 ... 体育之最12-11
-
官方:拜仁慕尼黑拥有38.2万注册会员,为世界体育俱乐部之最 官方消息,拜仁慕尼黑俱乐部拥有38.2万注册会员,为世界体育俱乐部之最。在拜仁慕尼黑2024年度股东大会上,俱乐部宣布,拜仁慕尼黑的注册会员达到382000名,为世界体育俱乐部注册会员最多的。而去年,拜仁慕尼黑的注 ... 体育之最12-09
-
36周岁的马龙老当益壮,他拥有多少之最?不仅仅是奥运“六金王” 10月20日,乒乓球名将马龙迎来36周岁生日。两个月前的巴黎奥运会,马龙加冕国内唯一的奥运“六连冠”殊荣,已经收获31个世界冠军的他是中国男子体坛多金王。其实,马龙在体育赛场创造的“之最”不仅仅这两项。请看: ... 体育之最11-27
-
45336人!中日之战创福建省单场体育赛事到场观赛人数之最 11月19日晚,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第6轮,中国队在主场1-3不敌日本,本场比赛共有45336人到现场观战,创造了福建省单场体育赛事到场观赛人数之最。本场比赛的举办地是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白鹭体育场,该体育场在 ... 体育之最11-27
相关文章
- 中国田径史之最十个
- 官方:拜仁慕尼黑拥有38.2万注册会员,为世界体育俱乐部之最
- 36周岁的马龙老当益壮,他拥有多少之最?不仅仅是奥运“六金王”
- 45336人!中日之战创福建省单场体育赛事到场观赛人数之最
- 今天他喜获国家荣誉称号,6创乒坛之最,率27人44次夺世界冠军
- 国羽男单四大之最,他们在干什么吃呢?
- 盘点巴黎奥运会引人注目的十之最
- 国乒八大之最
- 世界十大运动排行榜,足球和游泳双双入榜
- 十大最受欢迎桌游排行榜,《优诺纸牌》位居第一名
- 无愧梦之队!中国跳水首次大包大揽,已获55枚奥运金牌为各项目之最
- 巴黎奥运会 截止目前,关于中国体育代表团五个之最[玫瑰]:
- 截止目前粗略总结了一下,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六个之最:
- 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六个之最,陈梦成最悲情金牌获得者
- 截止目前,粗略总结了一下!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六个之最
- 奥运会历届之最有哪些!104岁对决, 46岁萨哈基安战胜58岁曾志英
- 冬天刚到,昆明这几家温泉就火了!来看看哪家才是昆明温泉之最
- 十大运动员之最,格林获选最危险,邓肯最被低估,勒布朗最重要。
- 中国游泳队又一全球之最!巴黎奥运前每人接受21次兴奋剂检测!
- 体育场地之最
热门阅读
-
NBA75大球星官方完整名单 02-15
-
世界十大顶级体育赛事:奥运会居第二,世界杯局魁首 08-23
-
2022热门网游排行榜前十,英雄联盟位居第一宝座 09-02
-
steam免费游戏排行榜前十名,不用花钱又好玩 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