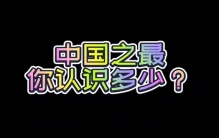藏书典籍之最!描述中国书友交往的故事,配图珍美,妙趣横生

【一〇】金粟山写经
癞蛤蟆连天鹅屁也吃不到了
“金粟山写经”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上,是1998年秋天的嘉德。我早就听说过金粟山这个名称,因为无论哪本讲古籍的书,几乎都会提到金粟山,而直到嘉德这场拍卖会,我才第一次看到实物。当时我请工作人员拿出这卷经,因为玻璃柜台的长度,打不开,于是,把该经摊在地上。工作人员递给我的时候,我觉得这卷经还略有分量,此经已被装裱成了一个手卷,摊在地上打开时,看到了原写经存有两纸,余外则是长长的拖尾,后面写着几段跋语,经的字体很是规整整齐,每个字之间,不是缺少变化而是完全没有变化,远不如唐人写经字迹的千姿百态。此经的估价是三万八至四万八千元,而原经的长度不超过两米,以我当时浅陋的见识,唐人写经的均价,平均是一米一万元,而金粟山是宋代写经,我觉得从年代上论,就比唐人写经低了一个档次,如此比较下来,花同样的钱,如果去买唐人写经,则感觉更有价值。然而,此经毕竟很有名气,我还是决定在拍卖场中试试运气。该经以三万五千元起拍,我追到五万元放手,被他人以五万五千元买去。当时觉得自己出的这个价格已经高于行市,竟然还有人跟着竞价,真是太不了解行市了。然而,随着后来自己版本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强烈地知道自己当时因为无知,做出那样的决定是多么愚蠢,每当我想到这件事,都后悔不迭。
金粟山在今天的浙江海盐县西南,山上有座金粟寺,在北宋熙宁元年(1068),金粟寺编了一部《金粟山大藏经》,据说有万余卷。此经所用的纸张很特别,据说是用桑皮和楮皮制成,反正两面均涂白蜡,并且砑光,又浸药水使之发黄。该经名气极大,因其纸质之佳,后世多想仿造,然而却始终制作不出金粟山所用纸的质地。藏书家吴骞在《尖阳丛笔》中说:“今则金粟山宋藏经纸,且不能仿。”其实此纸乾隆时在宫内仿制过,这种仿制纸我见过多张,就质量而言,要比真正的金粟山藏经纸差很多。明人胡震亨在《海盐县图经·杂识篇》中写道:“金粟寺有藏经千轴,用硬黄茧纸,内外皆蜡,摩光莹滑,以红丝栏界之。书法端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墨光黝泽,如髹漆可鉴。纸背每幅有小红印,文曰‘金粟山藏经纸’。有好事者,剥取为装潢之用,称为宋笺,遍行宇内,所存无几。”
由胡震亨的这段话可知,明代很多人就把金粟山纸揭成两层,作为装潢之用,故而使得该经在明代已所剩无几,到今天则真称得上是凤毛麟角了。由此他说到“书法端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恰恰是说明这种整齐划一的书法是该经的特色所在,而我却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种缺少变化的字体,没有书法美感,拿优点当缺点来看,我得不到这件宝贝也没什么可说的。
此场拍卖过后十年,这十年中我再没能看到“金粟山写经”的身影,随着对该经的了解,越看越觉得此经写得如此漂亮。这个世界上不缺少美,缺少的是有审美能力的人,我为自己的无知备受了十年的煎熬,到了第十一年,在我觉得自己跟该经再也无缘时,它竟然又出现了。
己丑秋,德宝举办了佛经专场拍卖会,本专场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一卷“金粟山写经”,也是裱成一个旧手卷,包首的白绫签条上写着“唐人写中阿含经音释”、“过云楼鉴藏第零零零贰号”,由此可知,该经出自过云楼,并且是过云楼所藏的第二号藏品,由此可见其地位之高。在清代,学界认为“金粟山写经”是唐代所写,经过后世研究,现在学界又定为北宋。该经所抄内容是中阿含经音释,存卷三十一至卷四十,总计四纸,起拍价为五十万元,参考价则标为六十万至八十万元,在拍卖图录中,同时标出起拍价和参考价,是德宝公司首创。以我此时对金粟山的了解,再加上行市,我觉得该经至少能拍到一百万以上。开拍前的几天,不断有书友来电话,问我对此经的看法,其实我很担心出现这种局面:来电话的人多说明关注的人就多,那么与之相反,捡便宜的概率则越来越低。尤其有的朋友会直率地说,希望我能相让,尽管我不愿当这种道貌岸然的大头,但书友的情意总比某部书要重要许多,谢其章兄曾经有过一句名言,他说书友间的关系是“又勾结又斗争”,我觉得他形容得很准确。但是我已经习惯于这种温良恭俭让,兄弟相残的事儿还真的下不了手。
来电话的朋友中有赵平先生,平常聊天时,是很好的朋友,但我最怕在拍前接到他的电话。他有自己独特的收藏观,他搞收藏,不分门类,不搞系列,只买每个门类中间的最好或者最有升值潜力者。我在他家看到他所收藏的瓷器、木器、手稿、善本等,每件都有独特的说法,我觉得这是金融投资方式中的价值投资,这种投资方式准确而又有效率。按照李嘉诚的观念,干一行爱一行,是不正确的一种投资观,爱上了自己的事业,也就意味着是用情感代替了理智,同样也就失去了冷静的价值判断。而我恰恰就犯此忌,但深知如此,又难以改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慢慢看出来了自己在投资方面不可能有什么出息。这一天,赵先生来电话,当然是为这件“金粟山写经”,尽管我也想要,但并不能因为我想要,就跟他人去贬低拍品的价值,我仍然告诉他这件写经没问题。以赵兄的冷静态度,我想他应当已经问过数位专家,他打电话给我,我揣度他的心理,应当是暗示我他要得到此经。
拍卖的时候,果真有许多人都争抢这件金粟山,我觉得不能就让别人这么轻易地捡到便宜,于是,也跟着争抢起来,举到了一百二十万,就感觉到了吃力。佟泽民兄在我面前说,你不举了,那我接着举。他举到了一百八十万也停了下来。后面还有一位不认识的人跟赵平兄接着争抢,直到二百零七万,才被赵兄拿下。
拍卖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脑子中一直还盘旋着这卷经,我马后炮地认为这个二百零七万其实挺值的。这卷经听说是由德宝的老板陈东先生从欧洲征集回来的,我没有找陈东先生确认过是否如此,但来自海外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经的内在价值并没有被人们真正地认识到。以此经的名气,再加上其稀有程度,如果再出现一卷,其价格恐怕翻一番也难以到手。我错过了这一卷,今后能够买得“金粟山写经”的概率就更加渺茫了。我觉得买书有时候是一种心态,尤其在值与不值之间摇摆,跟见到某书时手头的钱是否充裕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样一部书,在缺钱时,我总觉得价格很贵;而过一段又有钱了,马上会觉得那卷经或者那部书当时那么便宜我为什么不买。
德宝拍完此经后的五年,嘉德古籍部经理宋皓女士给我来电话,命我到其公司鉴定一批古纸。我在会议室中,看到了一大批旧纸,分成了几十幅,如此大量的古纸,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宋经理告诉我,这些纸是一家所出,此人收藏了几十年,她一次性征集到手,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大量的古纸上拍,她决定对这些纸张搞一个专场,担心的是这些纸被人买去后,如果继续珍藏,当然是好的结果,但也有可能拿去成了造假画的材料。当时我看到的这批纸中,最难得、价值也最高的,则是一张空白的金粟山藏经纸,“金粟山写经”不论实物还是图片,我已经见过多件,但是空白的金粟山经纸,却仅见过这一张,于是我对着它仔细审看了一番。宋经理看我如此翻来覆去地看,担心地问我是不是假的,我以自己有限的知识认定该纸是真品无疑。宋经理笑着说,此纸应当问题不大,因为纸的主人最看重的就是这张“金粟山”,理由是纸主人的堂号叫“金粟轩”。
此纸的估价是十万到十五万元,当时我很想把它买到手,可是回来后冷静想想,觉得自己得不到“金粟山写经”,而得到一张空白的写经纸,多少有点差强人意。范进中举前,他老丈人骂他想中举是癞蛤蟆想吃天鹅屁,我觉得这个“屁”字用得很传神,我得不到“金粟山写经”,而得到一张写经纸,就有如吃不到天鹅肉而吃到了天鹅屁。想了想,这个屁还是让别人去吃吧。然而,这个屁却最终拍到了二十六万。看到这个结果,我又犯病地开始后悔,到此时才醒过味来,得不到此纸,连屁也吃不上嘛。
大家都在看
-
厦门有哪些中国之最?这篇文章告诉你! 厦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不仅有着迷人的风光,还藏着许多令人称奇的“中国之最”。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吧! 交通工程之最 翔安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条海底隧道。它于2005年开始建设,2010年正式通车,全长约8. ... 中国之最12-17
-
中国高铁之最,你都知道多少呢?? 我国高铁之最你都知道多少?·国内最长的高铁线路是徐新高铁,东起江苏连云港,西至新疆乌鲁木齐,途经7个省和自治区,全长3176公里,相当于直接横穿整个中国。·国内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线路是京沪高铁,运营速度可 ... 中国之最12-08
-
中国之最,你认识多少呢? 中国之最你认识多少?·中国的国酒是?答案:茅台。·中国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答案:乌鲁木齐。·中国的国宝是?答案:曾母暗沙。·中国最北端是?答案:漠河县。·中国的国树是?答案:银杏。·中国的国宝是?答案 ... 中国之最12-05
-
中国 15 个 “景观之最” TOP1,你打卡过几处? 中国15个景观之最TOP1清单,他打卡8处还欠西沙丹巴他叫老白,户口在成都,身份证照片还停在二十多岁那张。换言之,人不年轻了,还爱跑。他说要按《中国国家地理》那份15个“景观之最”来,一个一个去看,别搞花里胡 ... 中国之最12-01
-
新疆巴楚,拿下“中国之最”! 10月24日第六届新疆喀什丝路文化胡杨节暨巴楚县第十五届胡杨文化旅游季开幕式在巴楚县红海景区尉头洲城门举行活动中巴楚县凭借约326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荣获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颁发的“拥有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 ... 中国之最10-30
-
国内之最!武荆宜高速汉江特大桥主塔封顶 荆楚网(湖北日报网)讯(通讯员王翔、王铭楷、王子明)10月28日上午,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浇筑到位,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武荆宜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汉江特大桥主塔塔柱顺利完成施工,标志着这座国内 ... 中国之最10-30
-
中国状元之最 中国本是一个官本位思想特别严重的国度,历代王朝皆奉行“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民间亦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人生信念,而读书人里面的number one则就是我们常说的状元了。中国科举时代究竟有多少状元呢?据 ... 中国之最10-28
-
收藏!20个必知中国之最,带娃边看边涨知识,满满家国自豪感 家长们快码住!说起中国之最,可不止山河湖海那么简单!从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到世界最长的京杭大运河;从最早的造纸术,到如今的高铁技术……这些藏在生活里的中国之最,既能帮娃拓宽知识面,又能让他们直观感受 ... 中国之最10-25
-
新疆八大世界之最和八大中国之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八大世界之最和八大中国之最世界之最1. 世界最长的沙漠公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北接轮南油田公路网与314国道连通,南与315国道相接,全长522千米,是世界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最长的公路。 2. ... 中国之最10-20
-
中国世界六大之最 中国第六大世界之最:全球创新霸主崛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最新报告:中国创新排名跃升全球第十,成为唯一进入前十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标志着全球创新格局迎来历史性转变。就在昨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 ... 中国之最09-20
相关文章
- 芙蓉国评论丨内陆省份为什么也能成长起这么多中国之最、世界第一?
- 内陆省份为什么也能成长起这么多中国之最、世界第一?
- 中国世界六大之最
- 中国之最二十条
- 北京司马台长城:被誉“中国长城之最”,藏着5大逆天奇景
- 🌹一定给你家的孩子收藏起来: 中国之最
- 细数汉长安城的中国之最
- 此生必去的50个中国之最,集齐了祖国所有美景密码,你去过几个?
- 中国大学之最,你知道几个?
- 你知道的中国之最都有哪些?
- 这100个中国之最,你竟有大半都不知道?
- 你还知道哪些中国之最?
- 安徽冷知识:推荐安徽这21个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你还知道哪些
- 中国各省之最盘点
- 中国10个此生必去的绝美之地,你打卡过几个
- 200亿工程冲刺收官!大榭石化聚丙烯装置创国内之最,6月投产在即
- 中国最火,最值得去的两座古城之争:四川阆中硬刚山西平遥,太牛
- 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中国经济最急迫的地方,并不在美国
- 中国最让美国惧怕的,不是经济体量,而是这三种超强能力
- 中国大陆最南的浪漫之约,52O世界爱情角特别话动
热门阅读
-
房中术素女经秘戏图本,我国古代性文化的鼻祖(图) 07-10
-
雷锋怎么死的?当时医疗条件差导致耽搁抢救 07-11
-
十大上海留学中介排名 想要有所成就就选它们 06-22
-
中国黑社会老大排行榜,最仗义东北乔四爷绝壁第一 06-23
-
中国第一条地铁建于哪里:北京地铁建于1965年 01-15
-
中国十大未破杀人惨案:悬案桩桩手段残忍无比 06-18
-
中国十大最漂亮的女人排行榜 中国最美的女人有哪些 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