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之瓦尔登湖
宇飛/整理
《瓦尔登湖》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

图片来源网络共享
瓦尔登湖的风景只好算粗线条,尽管很美,还是说不上壮观;不经常光临或者不在湖边居住的人,对它也不是特别关注;然而,瓦尔登湖以它的深邃纯净著称于世,值得对它详尽描述一番。原来它是一口清澈而黛绿的井,半英里长,周长一又四分之三英里,面积约有六十一英亩半;松树和橡树林中央,有一股终年井喷的泉水,除了云雾和蒸发以外,压根儿看不到它的入水口和出水口。周围的山峦陡然耸立,高出水面四十到八十英尺,虽然在东南角高达一百英尺,在东端更是高达一百五十英尺,绵延大约四分之一英里或者三分之一英里。
它们清一色都是林地。我们康科德境内的水域,至少具有两种颜色,一种打老远就望得见,而另一种更接近本色,在近处才看得出。第一种更多取决于光线,随着天色而变化。在天气晴朗的夏天,从不远处看去,湖面呈现蔚蓝色,特别在水波荡漾的时候,而从很远的地方望过去,全是水天一色。赶上暴风雨的天气,水面有的时候呈现深石板色。不过,据说海水在大气层中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却是今天蓝,明天绿。白雪皑皑时,我看到过我们这儿河里,水和冰几乎都是草绿色。
有人认为蓝色是“纯净水的颜色,不管它是流动的水,还是凝固的冰”。反正直接从小船上看湖面,倒是看得出非常不一样的颜色。瓦尔登湖一会儿蓝,一会儿绿,哪怕是从同一个视角看过去。瓦尔登湖位于天地之间,自然兼具天地之色。从一个山顶上望过去,它映现出蓝天的色彩,而从连岸边的沙子你都看得到的近处看,它却呈现出先是淡黄色,继而淡绿色,同时逐渐加深,终于变成了全湖一致的黛绿色。在有些时候的光线下,哪怕是从山顶上往下俯瞰,毗邻湖岸的水色也是鲜灵灵的绿色。有人认为,这是草木青葱返照的缘故,但在铁路道轨沙坝的映衬下,湖面依然是绿幽幽的;待到春天还没有叶茂成荫,这时湖光山色也不外乎是天上的湛蓝色与沙土的黄褐色掺在一起的结果,堪称瓦尔登湖彩虹般的色彩。
入春以后,湖上冰层因受从湖底折射上来的、又透过土层传来的太阳热量而变暖,于是首先被融化,在中间仍然冻结的冰凌周围,形成了一条狭窄的小河。正如我们的其他水域一样,每当天色晴朗、水波潋滟之时,水波表面会从合适的角度映出蓝色的天空,或者由于糅合了更多亮光,如果稍微远点望过去,湖面仿佛呈现比天空本身更深的湛蓝色;此时此刻,泛舟湖上,从各个不同的视角观看水中倒映,我发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不可名状的淡蓝色,有如浸过水的或者闪闪发光的丝绸和利剑青锋,却比天空本身更具天蓝色,它与水波另一面原有的黛绿色交替闪现,只不过后者相对来说显得有点儿浑浊罢了。
那是一种类似玻璃的绿里泛蓝的色彩,跟我的记忆里一样,有如冬日夕阳西沉时从云层里呈现出一片片蓝天。反正举起一玻璃杯水,往亮处看,它里头好像装着空气,一样没有颜色。众所周知,一只大玻璃盘子是略带一点绿色,据制造玻璃厂商说,是由于玻璃“体厚”的缘故,但同样都是玻璃,块儿小的就没有颜色了。至于瓦尔登湖该有多少水量,才会泛出绿色,我倒是从来没有验证过。
人们直接俯视我们河水,河水是乌黑的或者深棕色,而且如同大多数湖里的水一样,会给洗湖浴的人蹭上一丁点儿淡黄色;但是瓦尔登湖水却是如此纯净赛过水晶,使洗湖浴的人躯体洁白有如大理石一般,而且怪得出奇的是,此人的四肢给放大了,同时也给扭曲了,产生了一种骇人的效果,值得米开朗琪罗好好研究哩。
湖水如此晶莹剔透,一眼就看得到二十五英尺或者三十英尺深的湖底。你光脚踩水,可以看见好多英尺深水下,有成群的鲈鱼和银色小鱼,它们也许只有一英寸长,但是前者一道道的横着花纹倒也很容易辨认出来,你会觉得,它们必定是苦行修炼的鱼种,才到那里寻摸生计的环境。
好几年前的冬天里,有一回,我在冰层上凿洞钓狗鱼,我上岸时把我的斧子扔回冰层去,不料,仿佛神差鬼使似的,只见那柄斧子在冰层上滑出去了四五杆远,正好掉进一个冰窟窿里头去了,那儿水深二十五英尺。我出于好奇心,伏倒在冰层上往那个冰窟窿里头瞧一瞧,只见那柄斧子侧向一边,斧柄朝天竖起,随着湖水的脉动来回摆动,要是我不去打扰它的话,本来它说不定会在那儿就这么着直立下去,晃呀晃呀,随着时光流逝,直到斧柄烂掉为止。
我就在斧子的上方,用我带来的冰凿子又凿了一个窟窿眼儿,用我的刀子砍下我在近处寻摸到的最长的一根白桦树枝,枝头上打了一个活结套,随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下去,套住斧柄上凸起的一块疙瘩,用系住白桦树枝的一根绳子往上拉,就这么着把那柄斧子给拉上来了。
湖岸是由一长条好似铺路用的滴溜滚圆的白色石子筑成的,除了一两处小小沙滩以外,在许多地方都非常陡峭,纵身一跃正好落到没顶深的湖水中;要不是湖水晶光锃亮得出奇,你断断乎看不见湖底,除非湖底在对面升了起来。
有人认为,瓦尔登湖是湖深没有底的。湖水不论在哪儿也不浑浊,偶尔观湖的人还以为湖底压根儿连水草都没有,至于看得见的草木,除了不久前被水淹过的、原本不属于湖的那些小小草地以外,哪怕是再仔细地查看,也确实看不到菖蒲或灯芯草,连一朵百合花都没有,不管是黄色的还是白色的,至多只有一两片心形叶子和河蓼草,说不定还有一两片眼子菜;反正置身水中的人也许压根儿都看不出来;这些水生植物,好像如同它们赖以生长的湖水一样洁净、晶莹透亮。岸石延伸入水有一两杆远,湖底就是清一色的沙子了,只有在最深的地方通常会有一点儿沉积物,也许是历经好多个秋季树叶飘落、沉淀腐烂的缘故,甚至在仲冬时节,鲜绿色的水草也会随着铁锚一起浮出水面。
往西大约两英里半,一个叫九亩角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湖,那就是白湖。虽说方圆十几英里以内的湖泊十之八九我都很熟稔,可我还没有见过第三个湖具有如此纯净赛过井水的水质。这湖水也许古往今来各民族全都饮用过、赞赏过、测量过,随后也就相继消失了,唯有这湖水依然碧绿澄清。一个春天都没有间断过!说不定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那个春天早晨,瓦尔登湖早就存在了,甚至就在那个时候,随着薄雾弥漫和南风拂面而来的是一场蒙蒙的春雨,打破了湖上的平静,飞来了成群的鹅和鸭子,它们全然不知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一事,觉得能有如此这般纯净的湖水,它们早就心满意足了。
即使在那个时候,这个湖已开始时涨时落,湖水碧绿澄清,呈现出今日里的色彩,仿佛具有蓝天的特征,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瓦尔登湖和天上露珠的蒸馏器。谁知道,有多少种无人记得的民族文学作品把这个湖称为卡斯塔利亚泉?要不然在古代神话中的黄金时代,又有多少山林水泽的仙女们曾在这里居住过?这就是康科德冠冕上的第一颗滴水宝石。
湖水时有涨落,但不管它有没有规律或者周期,都是无人知晓,尽管有好多人惯常都会不懂装懂。一般说,湖水冬天高,夏天低,这和大气的潮湿干燥并没有相应关联。我还记得,倘若跟我住在湖边时相比,湖水什么时候落下去一两英尺,什么时候涨上去一两英尺,什么时候又会涨上去至少五英尺。有一条狭长的沙洲径直延伸到湖中,沙洲一边的湖水非常深,离主岸六杆远,大约在1824年,我在这沙洲上煮过一锅海鲜杂烩浓汤,时隔二十五年,要想再煮也是不可能了;另一方面,我已告诉过我的朋友们,说几年之后,我常驾着小船到隐蔽在树林子幽深处的小湾里去钓鱼,离他们知道的湖岸才不过十五杆远,可现在那儿早已变成了一片草地。
他们听后老是不大相信,可是湖水两年来不断在上涨;现在,1852年的夏天,比我住在那里时高出了五英尺,或者换句话说,相当于三十年前的水位高度,岂不是又好到那块草地上钓鱼了。从外表看,水位落差有六七英尺;可是从周围群山流下来的水量并不大,水位上涨一定是跟影响深处泉源的原因有关。就在同年夏天,湖水又开始回落了。
引人注目的是,湖水这种时涨时落,不管它有没有周期性,好像都需要好多年方能完成。我曾经观察到一次湖水上涨和两次湖水部分回落,我估摸,再过十二年或者十五年,湖水又会回落到我过去所了解的低水位了。东端一英里的佛林特湖,因湖水流入和流出而时有涨落,那些介于两者之间的小湖,则和瓦尔登湖的水情大致相仿,近来也和后者一样涨到了它们最高水位。根据我的观察,白湖的水位也是如此。
瓦尔登湖时涨时落,间隔时间很长,至少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湖水处于这种很高的水位,已有一年左右,尽管环湖行走不易,但从上次涨水以来,沿湖长出来的灌木丛,以及诸如北美油松、白桦树、桤木、大齿杨等等树木通通给冲走了,等到水位再次回落时,就留下光秃秃的湖岸;因为瓦尔登湖跟许多湖泊和每天水位有涨落的河流不一样,水位最低时,湖岸偏偏最干净。临近我住房的湖边,一长溜高达十五英尺的北美油松全被冲走,好像用杠杆给掀翻似的,从而止住了它们向湖岸的扩展;这些树木躯干的大小,表明上次湖水上涨到这种高度以来已有多少个年头了。
通过这种涨落,瓦尔登湖对湖岸拥有了主权,因此,湖岸仿佛被剃光了胡子,使那些树木不能凭借所有权来侵占湖岸。这些瓦尔登湖的嘴唇上一茎胡子也都长不出来。湖水时不时地舔着自己的下巴颏儿。湖水涨高时,桤木、柳树和槭树淹没在水中的树根周围,都浮起大量纤维似的红色根须,长达好几英尺,高出地面三四英尺,一个劲儿来保护它们自己;我知道,湖岸那一带有一些高高的乌饭树灌木丛,通常不结果子,但在这种条件下倒是会结出丰硕的浆果来。
赶上风平浪静的天气,你坐在小船上,可以看到,湖的东头沙滩附近那一带,水深八英尺至十英尺,还有在湖的别处,也可以看到一些圆形堆垛,高约一英尺,直径六英尺,由比鸡蛋个儿还小的圆石子码成,周围全是光溜溜的沙子。起初你会纳闷,这是不是印第安人故意在冰层上堆叠这些圆石,待到冰层融化时,就一块儿沉到了湖底;可是,这些圆石码得太齐整匀称,里头有些圆石显然也太新鲜,不像人工堆叠。它们与河里找到的石子一模一样;反正这儿既没有胭脂鱼,也没有七腮鳗,我可闹不清楚那些圆石堆是由哪些鱼码起来。也许它们就是银色小鱼的窝儿吧。这些圆石堆给湖底平添了几分喜人的神秘感。
湖岸错落有致,一点儿都不单调。在我的心目中,西岸是犬牙交错的深水湾,北岸较为险峻,而南岸呈扇贝形,很漂亮,一连串岬角相互交叠,不由得使人想到岬角之间还有好些人迹罕至的小水湾。湖水边沿耸立的群山之间,有一个小湖,从小湖中央放眼四望,你会欣赏到在森林映衬下从来没有过的绝妙的美景;因为森林映在湖面的倒影,不但形成了最佳的前景,而且,由于迂回曲折的湖岸,也成为它的最自然、最宜人的边界线。这儿与板斧砍出来的林地不一样,与毗邻湖边的耕地也不一样,既无斧凿的痕迹,又无不完美之感。树木享有充分的空间可向水边扩展,每一棵树都冲着这个方向伸展出最富有活力的枝杈。


在这儿,大自然编织了一道天然的花边,一眼望去,从湖边低矮的灌木丛蜿蜒向上,一直可以望到那些参天树木。在这儿,你看不见有什么人工痕迹。湖水冲洗堤岸,有如一千年前一模一样。
湖——在天然景色中最美、最富有表情的就数它了。它是大地的眼睛;人们观湖,可以掂量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湖畔水生树木,是仿佛给它镶边的修长的睫毛,而四周树木葱郁的群山和峭壁,则是它的悬挑的浓眉了。
9月间的一个下午,风平浪静,薄雾迷蒙,湖对岸的轮廓显得模模糊糊,此时此刻,站在湖的东头平坦的沙滩上,我方才恍然大悟,“湖面如镜”这种说法究竟是从何而来。你要是把头倒转过来看湖,湖就像一条最精致的薄纱悬挂在峡谷上空,在远方松林的映衬下闪闪发光,把大气一层一层地分隔开来。
你会觉得,你可以从它底下衣不沾湿地走过去,一直走到湖对面的群山那里,而掠过湖面的燕子也可以在湖上栖息。有时候,那些燕子果真向它俯冲下来,好像一时失误,稍后才恍然大悟。你朝西头湖岸抬头望去,不得不举起两手遮住自己的眼睛,挡开地地道道的阳光和从水中反射上来的阳光,因为这两种阳光同样亮得耀眼;你要是用挑剔的眼光,在这两种亮光之间审视湖面,就会看到它端的是波平如镜了;余外只见一些贴水掠飞的昆虫,遍布整个湖面,彼此错开相同间距,在阳光下飞来飞去,在水面上产生了可以想象到的最精美的闪光来;也许间或还有一只鸭子在梳理自己的羽毛,或者,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有一只燕子贴水低飞,快要碰到水面似的。也许从远处望去,一条鱼儿在半空中画出了一道三四英尺的弧线,在它跃出水面时映出一道闪光,在它钻进水里时又映出了一道闪光;有时候,这一道银光闪闪的弧线还会整个儿显现出来;要不然,也许有一根蓟草漂浮在湖的什么地方,鱼儿冲它一跃,湖面上也会激起一圈圈涟漪。
这时,湖面像熔化的玻璃,冷却了但还没有凝结,里头绝无仅有的尘埃也显得纯洁而优美,可谓白璧的微瑕。你经常会看到一片更光滑、更幽暗的水域,仿佛有一张看不见的蜘蛛网,把它和别的水域截然分开,成为水中仙子在那儿憩息的水栅。你从山顶上可以俯看到,几乎所有的水域都有鱼儿在跳跃;在这波平似镜的水面上,只消一条狗鱼或者银色小鱼在捕食一只小虫子,就会把整个湖面的平静给搅乱了。
真是神极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却显现得这么精巧——这种鱼类伤生害命的事终必败露——我打老远高头就清晰地看到一圈圈直径为六七杆的波浪形在四周围扩散。你还会看见一只水蝽(拉丁文学名Gyrinus)在平滑的水面上不停歇地滑过去了四分之一英里;它们轻轻地在水面上犁出了波纹,两道分叉线形成了明显的涟漪,可是长足昆虫在水面上滑行,却不会留下看得见的涟漪。湖面上一掀起波浪,长足昆虫和水蝽连影儿都见不着了。
但是,赶上风平浪静的日子,它们就会离开自己的避风港,好像探险似的,凭着一时冲动,打从湖边出发,一个劲儿往前方滑行,直到滑完全程为止。入秋后晴朗的一天,坐在高高的山头的树桩上,沐浴在温煦的阳光里,俯瞰瓦尔登湖景,仔细捉摸那一圈圈涟漪,一刻不停地雕刻在有着天空和树木倒影的水面上,要不是这些涟漪在晃动,连水面也都看不见呢——这真的是令人舒心的快事啊!在这么浩淼的水面上,什么干扰都没有,即使有一点儿,很快就会缓解消失,让人安静下来,好像在湖边汲取一壶水,颤动的水波流到了岸边,一切复归平静。
鱼儿从水中跃起,小虫子落到了湖里,不外乎通过一圈圈涟漪和优美的线条表述出来,好像这是泉水不断地在向上震颤、井喷。是它的生命在轻轻地搏动,是它的胸脯在上下起伏。那是欢乐的激动,还是痛苦的战栗,全都说不清楚。湖上好一派安谧的气象啊!人类的劳动如同在春天里,又在闪闪发光。是啊,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枝条、每一颗石子、每一张蜘蛛网,到了午后时分都在闪闪发光,宛如春天早晨它们身上沾满的露珠似的。船桨或者小虫子的每一个动作,也都会发出闪光;听那船桨的欸乃声,该有多美啊!
赶上九十月里这么一天,瓦尔登湖俨如十全十美的森林明镜,四周镶上圆石子,依我看,这些圆石子十分珍贵,可谓稀世之宝。说不定地球上再也没有一个湖,会像瓦尔登湖这样纯美,同时又这样浩渺。邈邈乎来自天上的水啊!它不需要护栏。多少个民族来了又去了,都没有玷污过它。它是一面石头砸不碎的镜子,它的水银永远不会消退,它的镶边金饰大自然还在不断修补呢;风暴、尘垢,都没法使它永远光鲜的表面黯然失色——这一面镜子,凡是不洁之物落在上头立时会沉下去,被太阳底下雾气掸去尘埃,刷洗干净——这是一块拂尘布——往上面呵一口气也都留不住,只管自己直升到高空,宛如悬浮在湖上的朵朵白云,同时又清晰地倒映在湖面上。
泱泱的湖水,让空中的精灵出没无常。它不断从天上接受新的生命和旨意。它实质上在天地之间充当媒介。大地上只有草木随风摇曳,而水自身却被风儿吹起一圈圈涟漪。从一缕或者一片闪光里,我看得出风儿在轻轻地吹拂。我们能够仔细俯视湖的表面,真是匪夷所思。说不定我们将来终究也会像这样仔细俯视天空的表面,发觉一个更玄妙的精灵打从它上面掠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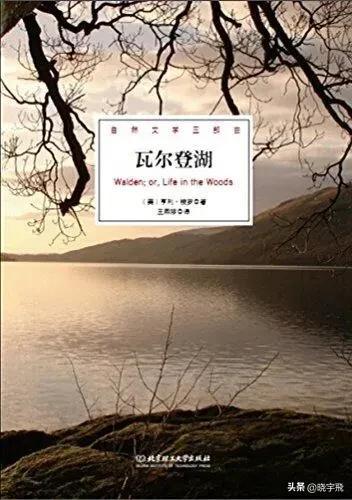
10月的后半个月,严霜降临,长足昆虫和水蝽终于销声匿迹;再往后到了11月,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通常湖面上绝不会被什么玩意儿激起涟漪来。11月的一个下午,持续好几天的暴风雨终于停了下来,但天上仍然阴云密布,雾气迷蒙,我观察到瓦尔登湖上光溜溜得出奇,连湖面都很难辨认出来;它虽然反射不出10月里光艳艳的色彩,却映照出了周围群山在11月间的暗淡色调。我尽可能轻轻地划着小船过湖,可是我的小船激起的波纹却一直扩散到我看不见的远方,使湖里的倒影泛出弯弯曲曲的形状。
我抬眼观望湖面,隐隐约约看见远处星星点点的微光闪烁不定,就像一些在水上掠过的虫子躲过严霜之后却在那儿扎起堆来了,或者说,也许湖面过于光溜溜,连泉水从湖底往上井喷,也依稀可见。轻轻地荡起双桨,来到了那些地点,我吃惊地发觉,四周全是数不尽的小鲈鱼,大约有五英寸长,在碧绿的湖水里呈深铜色,它们在湖中嬉戏,经常跃到水面上来,激起一圈圈涟漪,有时还会留下一些小小泡沫。
在如此透明、好像无底、映现云彩的湖水中,我好像乘着气球悬浮在空中,鲈鱼们则游来游去,依我看,如同飞翔或者盘旋似的,它们俨然是一群鸟儿打从我的下方或左或右穿过,它们的鳍有如全部撑开的风帆。瓦尔登湖就有好多这样的水族,显然它们要在严冬还没有落下冰帘、遮住它们头上广阔的天光之前,充分利用一下这个短暂的季节;有时,它们给湖面呈现出些许细纹模样儿,好像只是一丝微风拂过湖面,或是洒下几滴雨点罢了。
我漫不经心地渐走渐近时,它们大吃一惊,猛地拍击湖水,甩着尾巴激起了水花来,好像有人拿着一根刷子似的枝条在击水,眨眼间它们都躲到湖水深处去了。最后,湖上一起风,雾霭渐浓,浪儿开始翻滚,鲈鱼们比前时蹿得更高,半拉鱼身一下子蹿出了水面,形成上百个黑点子,三英寸长。
有一年,即使迟至12月5日,我还看到水面上有一些水花,以为一眨眼就要下大雨了,空中雾气弥漫,我急吼吼坐到划桨的位置上,冲着家径直划去;这时好像雨已经越下越大了,虽然我脸颊上还丝毫没有感觉到,可我估摸自己管保会淋成落汤鸡了。殊不知突然间那些水花连影儿都看不见了,原来水花是鲈鱼们激起来的,我的划桨声吓得它们潜入深水里去了,我目睹它们成群地消失得渺无影踪;就这么着,我衣不沾湿地度过了这天的下午。
上一篇:你所掌控的力量
大家都在看
-
江苏省兴化市之“最”盘点 兴化市,作为江苏省泰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不仅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在多个领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之最”。以下是对兴化市之“最”的详细盘点。一、自然之最1. 最大的淡水湿地保护区:兴化市 ... 自然之最04-09
-
江苏“之最” 江苏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和文化大省,拥有众多自然、历史、经济、文化领域的“之最”。以下是部分代表性内容:自然地理之最 1、最高峰:连云港云台山玉女峰,海拔624.4米,是江苏省地理最高点。 2、最大湖泊: ... 自然之最03-31
-
中国10大地理之最:探秘自然奇迹的巅峰与极限 ☆☆中国广袤的疆域蕴藏着无数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世界之巅的雪山、深不可测的峡谷、浩瀚沙漠、碧波万顷的湖泊,每一处地理之最都书写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探索吧!1.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珠 ... 自然之最03-29
-
中国自然与地理之最 1. 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约16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这里有沙漠、雪山、草原等多样景观,如喀纳斯湖的秋色、克勒青河谷的冰川群,以及神秘的罗布泊。 2. ... 自然之最03-24
-
江苏省兴化市海南镇之“最”盘点 海南镇,作为江苏省兴化市下辖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小镇,不仅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以其独特的“之最”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以下是对海南镇之“最”的详细盘点。一、自然之最1. 最美丽的湖泊风光:海 ... 自然之最03-21
-
海南地理与自然之最 1 、海南岛(本岛)四至之角最北角:文昌市木兰湾木兰角,北纬20-9-40;(木兰角)最南角:三亚市锦母角,北纬18-10-04;(锦母角)最西角:东方市八所镇鱼鳞洲鱼鳞角,东经108-36-43;(鱼鳞角)最东角:文昌市龙楼 ... 自然之最02-26
-
中国自然景观之最 中国的城市不仅以其独特的文化与历史闻名,还因其壮丽的自然景观而吸引全球游客。以下是一些中国城市在自然景观方面的“之最”:1.桂林山水漓江 :被称为“桂林三绝”,以其清澈见底、层峦叠嶂的江水和四周的山峰闻 ... 自然之最02-26
-
世界最小的海前十名:苏禄海上榜,第九位于日本 海洋让人感觉是一望无际,但有些海洋很小,虽然看起很小但储水量很大,里面有丰富的资源,能提供给人类,海洋是地球上最广阔的水体,排行榜123网查询各大平台,整理出世界最小的海前十名,其中马尔马拉海是世界上最 ... 自然之最02-20
-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排名:雅浦海沟上榜,第一位于西太平洋 海沟是海洋中两壁较陡、狭长、水深大于五千米的沟槽,是海底的最深处的地方,这些海沟分布在各大洋,地理位置复杂,有各种的海洋生物,排行榜123网查询了各大网站,整理了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排名。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 ... 自然之最02-20
-
世界最大的岛屿排行:本州岛上榜,第十加拿大第三大岛 岛屿是指四面换环水在涨潮时高于水面而形成的陆地,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有些岛屿上有丰富的资源,各种美丽的风景,适合人类生存,排行榜123网查询了各大网站,整理了世界最大的岛屿排行。 世界最大的岛屿排行 1.格陵 ... 自然之最02-20
相关文章
- 天然湖盐排名榜前十名:洛桑湖盐上榜,第七荷兰的
- 三角洲面积排行前十名:中国上榜两个,最后为埃及文明发源地
- 世界五大盐湖排名:第一是天空之境,死海上榜
- 世界最大的盐湖排名前十
- 游山玩水赏云海 矗立北京东边最高处的森林王国
- 白鹿的奇妙时刻:沉醉日照金山,感悟自然之美
- 湖州漂流之旅:激流勇进,畅享自然之魅
- 秋天最有仪式感的9件小事,做过5件,就很幸福
- 有一种农村叫浙江农村,真的顶
- 海外华文媒体走进江西庐山 感受自然与人文之美
- 白鹿镜头下的日照金山:自然之美的极致颂歌
- 看到65岁的山口百惠,再看54岁的鲁豫,才懂什么叫“自然才是美
- 米芾书法的“平淡”与“自然”
- 揭秘自然之最——海边治愈心灵的梦幻花园
- 揭秘自然之最——玻璃杯中的奇幻世界
- 2018全国适合养老的20座城市,丽江竟然排第一
- 秦岭自然保护地体系知道多少?
- 地球上奇迹最多的地带
- 自然界的奇迹:揭秘世界之最的十大自然奇观
- 吉尼斯之最:世界上最震撼人心的自然奇观!
热门阅读
-
张译和张铎,你真的能分清楚吗? 07-13
-
三年自然灾害毁灭了多少的东西,实属可怕 07-13
-
丹霞山阴阳石酷似男女生殖器,羞涩的人真的看不下去 07-13
-
世界上最高的十大山峰,珠穆朗玛峰稳居第一 07-13
-
俄罗斯十大城市排名:莫斯科第一,圣彼得堡第二 08-01
-
世界十大最缺水的国家排行榜,索马里位列第一 08-12


















